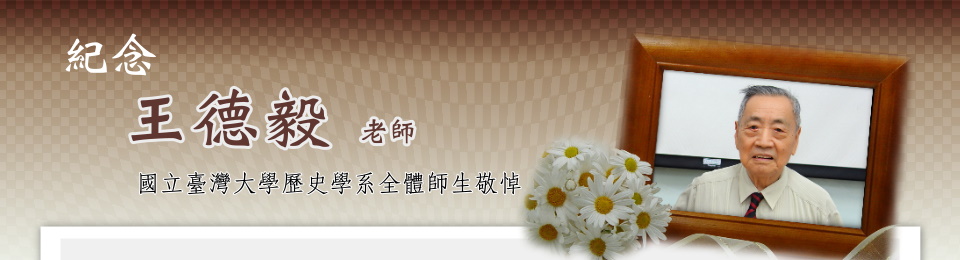| |
斯人已逝 功德長存
——痛悼恩師王德毅先生
張希清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
|
4月30日,我正在宋朝參知政事趙抃的故鄉浙江衢州,參加王瑞來教授《大宋名臣趙抃》新書發佈會暨趙抃勤廉風範文化交流活動。一同參加活動的中山大學曹家齊教授突然告知臺灣大學教授王德毅先生不幸于4月29日晚9時仙逝。聞知噩耗,一陣懵然,難以置信。十數天來,德毅先生的音容笑貌一直縈回腦際,除請家齊教授代為轉達沉痛悼念之意外,一直在搜集材料,準備寫一些追思的文字。今天(5月11日)是德毅先生舉行安息儀式之日,謹回憶聆聽德毅先生教誨40年來其中的三件事,以寄託哀思。
一、一字之師 終生難忘
我與德毅先生交往要追溯到40年前的1984年。當年秋天,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春樹先生應邀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並擔任歷史學系主任,遂發起召開「國際宋史研討會」。大陸由鄧廣銘師和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酈家駒研究員帶隊與會,臺灣則由中國文化大學宋晞教授和臺灣大學王德毅教授帶隊與會。另外,還有一些香港及歐美的宋史學者參加。此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不久,大陸與港臺尚無學術交流。對於大陸、港臺哪些學者參加?研討會日期、議題等問題,需要以通信方式反覆討論、協商。當時大陸方面的信函都是鄧廣銘師口授、由我起草以鄧先生的名義發出的,香港方面則是由李弘祺教授起草以張春樹先生的名義發出的。在信函往返的過程中,讓我瞭解到德毅先生的生平事蹟和道德文章。這次國際宋史研討會於1984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海峽兩岸三地及歐美學者共聚一堂,當面交流學術,取得了豐碩成果。這是1949年以來海峽兩岸三地宋史學界的第一次學術交流盛會,也是兩岸三地歷史學界的第一次學術交流盛會。德毅先生為開創兩岸三地宋史學界的學術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
1985年5月,鄧廣銘師與徐規先生共同發起,北京大學和杭州大學在杭州聯合主辦了第一屆中國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從1980年鄧廣銘師發起成立中國宋史研究會以來,每兩年召開一次中國宋史研究會年會暨國際宋史學術研討會。從1986年起,岳飛研究會也經常召開岳飛學術研討會。從2006年起,中國范仲淹研究會也經常舉辦范仲淹國際學術論壇。德毅先生從1991年7月到杭州參加「紀念岳飛誕辰888周年學術研討會暨岳飛研究會第三屆年會」之後,經常前來大陸參加有關宋史的學術會議。我作為鄧先生的學生和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助理(後任副主任、主任),經常與德毅先生見面,聆聽教誨。
1992年4月,我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發表了〈宋代殿試制度述論〉一文,認為宋太祖創立殿試制度,其目的不僅是為了「精辨否臧,克叶至公」,防止勢家壟斷科舉,致塞孤寒之路,更主要的是鑒唐之弊,收攬威權,在收兵權之後,把取士大權也收歸皇帝親自掌握,防止知貢舉官與及第進士結黨營私,以鞏固和加強趙宋王朝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其重要依據即是柳開《與鄭景宗書》。柳開的這封書信中記載:開寶六年,下第進士徐士廉「伏闕下,求見太祖。太祖夕召與之見,士廉即具道貢舉人事,請太祖廷試之,曰:『方今中外兵百萬,提強黜弱,日決自上,前出無敢悖者。惟歲取儒為吏,官下百數,常常贅戾,以其授於人而不自決致也。為天下國家,止文與武二柄取士耳,無為其下鬻恩也。』太祖即命禮部所中、不中貢舉人,到于殿廷試之,得百二十七人,賜登高第,開幸在其數。」宋朝殿試即自此始。我原來將「日決自上,前出無敢悖者」點破為「日決自上前,出無敢悖者」。這篇論文曾寄給德毅先生請教,先生即指出我將「前出」點破的錯誤,說「前出」是一個詞,不應點破。「前出」是一個軍事用語,意為派遣小股部隊到大部隊的前方,用於探路、偵察、掩護、排障等戰術用途。查《辭源》、《漢語大詞典》和《辭海》,均未見「前出」的此條,而是見於古籍的記載之中。德毅先生一眼看出我的斷句錯誤,可見其學識淵博,遠超常人。
宋人陶岳《五代史補》卷三載:「齊己作《早梅》詩,有『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之句。鄭谷改『數枝』為『一枝』,齊己下拜,時人稱鄭谷為『一字師』。」鄭谷是晚唐詩人,此後「一字之師」遂成為一個成語,宋人羅大經《鶴林玉露》、明人張岱《與周伯戩書》等均運用過。德毅先生即是我的「一字之師」。當然,德毅先生對我的教誨決不止於此,此後我經常將論著送給先生指正,先生教誨良多,「一字之師」僅為其中一例。雖為一字,但使我終生難忘。徐士廉「日決自上,前出無敢悖者」一語為我首先引用,我在《中國科舉考試制度》、《中國科舉制度通史》(宋代卷)等論著中再次引用時,均已按德毅先生的教誨改正,但現在有的學者引用徐士廉這句話時仍然沿用我過去的斷句錯誤,可能是被我誤導,希望予以改正。
二、特別邀請 恭與盛會
1995年12月,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史學系、史學研究所擬由文學院院長宋晞教授主持在臺北舉辦「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邀請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和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50餘位學者參加。當時,臺灣中國文化大學邀請了杭州大學徐規教授、河南大學王雲海教授、上海師範大學朱瑞熙教授等10位大陸學者參加研討會。那時海峽兩岸尚未「三通」,大陸學者赴臺,需經過香港,住宿一夜,第二天飛往臺灣。至於參加研討會的手續,更是十分複雜,在臺灣,不僅需要中國文化大學發出邀請,還需臺灣大陸委員會根據大陸學者提供的有關申請表格予以審查批准。在大陸,則需要學校與教育部的層層審查批准。
當年8–12月,我在韓國高麗大學歷史學系講學,很想參加這次盛會,但是無法與國內學者一道,通過正常辦理各種手續赴臺參會。德毅先生是臺灣學術組織「宋史座談會」的主持人之一,而宋史座談會是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的協辦單位之一。於是,我將參加會議的意願寫信告訴了德毅先生,並提交了論文〈宋代宗室應舉制度述論〉。德毅先生非常熱心,動用了許多關係,找了許多有關部門,作了許多擔保,克服了許多困難,終於給我辦理好了參加研討會的各種手續。從韓國的漢城(今首爾)到臺北,需要辦理入境手續,德毅先生又通過有關部門進行了妥善安排。12月26日,我終於如期從漢城飛到了臺北。其中的曲曲折折,可以借用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一句話:「不足為外人道也。」
參加中國文化大學舉辦的「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是我第一次去臺灣。到臺北之後,即受到德毅先生的熱情接待,當天中午即由他自己出資為我設宴接風。除德毅先生和我之外,還有幾位德毅先生的學生參加。宴會上盡是臺灣的美食。我不是美食家,30年前具體吃了哪些美食,現在已經記不得了,但是對喝純正的金門高粱酒,卻印象深刻。德毅先生接我來臺,十分高興,酒興很濃;我雖然不勝杯杓,但盛情難卻,也超水準發揮,喝了不少。總之,給人一種回家的感覺。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在臺北中央圖書館舉行,與會學者下榻於六福客棧。研討會及參觀臺北故宮博物院、中國文化大學期間,德毅先生與他的學生、作為觀察員與會的甯慧如碩士,多有照顧。記得一次由臺北中央圖書館返回六福客棧途中,與會學者乘坐的大巴堵車,德毅先生與我乘坐甯慧如碩士開的小轎車則先行順利回到了駐地。

出席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的學者,都是宋史學界的大家。如臺灣的宋晞教授、王德毅教授,大陸的徐規教授、王雲海教授,美國的陶晉生教授、包弼德教授,新加坡的陳榮照教授等。諸位學者的精彩發言、評議人的中肯評議,使我增長了許多學問,真是受益匪淺。如果沒有德毅先生的特別邀請和鼎力相助,我是不可能參與這次宋史學界的盛會的。我參加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之後又回到高麗大學,然後回到北大。此後不久,有人寫信給北大校方,告我通過不正常的途徑參加了臺灣的宋史學術研討會,是有問題的。北大校方認為我在韓國講學期間應邀到臺灣參加學術會議也正常,沒有問題。在當時這種氛圍下,德毅先生的特別邀請、鼎力相助,使我得以參加宋史學術研討會這一盛會,與宋史學界大家進行學術交流,更使我非常感激,永遠銘記。
三、傳記資料 嘉惠學林
德毅先生是臺灣宋史學界的領軍人物,長期主持臺灣宋史學界的「宋史座談會」。該座談會邀請臺灣地區或訪臺的宋元史學者報告目前關注的問題或進行的研究,並且進行共同討論。自1963年創會迄今,已舉行過220次聚會,編輯出版了36輯《宋史研究論集》,成為展示宋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園地。德毅先生長期擔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桃李滿園,著作等身,主要著有《李燾父子年譜》、《王國維年譜》、《洪邁年譜》、《姚從吾先生年譜》、《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宋史研究集》初集、二集;編有《清人別名字號索引》、《明人別名字號索引》、《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總目》、《宋會要輯稿人名索引》、《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合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合編)等。
德毅先生的突出學術成就是對宋代史學和宋人傳記的研究。對於其他學術著作暫且不論,現謹說一下主要由他編纂和增訂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該書是一部檢索宋人傳記資料的大型索引工具書。本索引共採用宋人文集347種、元人文集20種、總集12種、史傳典籍90種、宋元地方志28種、金石文8種,總計505種,其他單行的年譜、事狀、言行錄、別錄及期刊中屬傳記性質的論文尚未計算在內。全書所涉及的宋代人物共計2.2萬餘人,凡有事蹟足敘、言行可法、著述可考者,皆為之編撰傳記資料索引,且就收集所得為每人撰一小傳,註明生卒年、字號、籍貫、親屬、科第、仕履、事功、封贈、特長和著作等。全書共六巨冊、5,000餘頁。首冊附有引用書目,著錄所引書目的卷數、作者及版本,以便讀者查閱;末冊為《宋人別名字號封諡索引》,也非常適用。全書既是一部宋人小傳資料的彙編,又是一部收羅頗為詳備、檢索極為方便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工具書。本書自問世以來,使海內外宋代歷史、文學和哲學研究者獲益甚大,備受好評。鄧廣銘師總將《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放在案頭,以便隨手查閱,說這是宋史學者的必備之書。
《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從1968年開始編纂,到1976年由臺灣鼎文書局出版第六冊,歷時八年有餘。1977年又由德毅先生增訂再版。2001年再出版增訂第三版。1986年,時任中華書局編輯的王瑞來教授得到美國宋史學者轉贈的一套德毅先生增訂再版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中華書局認為此書堪為研究宋代文史哲學者的至寶,十分難得,決定影印此書。當時大陸尚未加入有關版權協議,遂不顧《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版權頁上所寫「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於1988年3月影印出版了中華書局版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大概由於當時海峽兩岸學術交流不通,中華書局影印《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事前既未徵得德毅先生同意,事後也未向德毅先生支付稿酬。多年之後,王瑞來教授見到德毅先生,當面向他致歉。德毅先生非常大度,認為中華書局翻印《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是嘉惠學林,沒有予以追究。
《宋人傳記資料索引》還成為「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的首批傳記資料來源。「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和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作建立的一個開放性的大型資料庫。2004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包弼德教授提出與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和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作,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負責將德毅先生增訂再版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的宋人傳記資料按照有關要求錄入「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我和鄧小南教授等與包弼德教授就「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的框架結構、資料錄入等問題,在北京和臺北進行了多次討論。2005年3–4月,我作為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應邀到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作訪問學者。在此期間,我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田浩教授一起到芝加哥參加亞洲年會。在亞洲年會期間,我和包弼德教授、田浩教授共進午餐,最後達成了合作協定。
2005年暑假期間,我即和鄧小南教授等組織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宋遼金史方向的博士生和碩士生,利用星期六和部分寒暑假的時間,將德毅先生增訂再版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的宋人傳記資料按照有關要求錄入「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研究生的勞務費由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按月支付。前後大概用了四年時間,完成了2.2萬多人宋人傳記資料的錄入工作。這是「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創立的良好開端。此後,陸續錄入了《元人傳記資料索引》、《明人傳記資料索引》等,截止今年2月,共收錄了53萬多人的傳記資料,成為一個規模龐大的資料庫,進行線上服務,為世界各國學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元人傳記資料索引》主要是德毅先生編纂的,《明人傳記資料索引》也是德毅先生參與編纂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等書為「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提供了最早一批傳記資料來源,成為「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的堅實基礎。可以說,沒有德毅先生編纂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等書,就沒有「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德毅先生編纂的傳記資料嘉惠學林。大家在使用「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進行學術研究之時,一定要銘記德毅先生最原始、最基礎的貢獻。
斯人已逝,功德長存。師恩難忘,永記心間。
願德毅先生在極樂世界永遠安息!
2024年5月11日於北京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