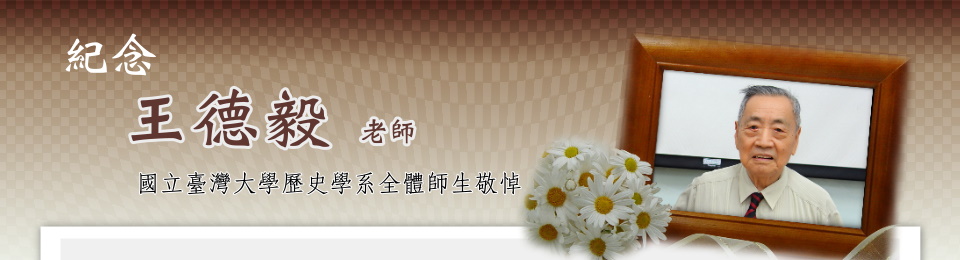| |
滿季雨殤訴不盡, 一腔悲切念師恩
——痛悼王德毅先生
曹家齊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
|
四月二十八日,家齊自廣州飛抵衢州,參加次日之王瑞來先生新著《大宋名臣趙抃》發布會暨趙抃勤廉風範文化交流活動。三十日晨,在酒店與王瑞來、張希清、顧宏義等幾位先生一起早餐,突接黃寬重先生微信:「剛才得知我的老師王德毅教授於二十九日晚上九時二十三分辭世。」看到此短信,頓覺頭腦一懵,早餐再無滋味。早知王先生久病臥床,且近日狀況不佳,但聞此消息,仍是難以自持,傷悲驟至。將情況告知幾位先生後,便回房給王師母孫國瑞老師打了電話。師母告知,先生後事將由黃寬重等先生幫忙料理,先生三子亦已買好機票,即將自美國返臺。電話中,聽師母聲音悲傷不已,心有同戚,卻唯有再三安慰!
當日本計劃返穗,因暴雨故,航班取消,改飛深圳,又被取消,只好等待五月一日返回。被迫留衢,便隨張希清先生和張師母羅雪娟一同去江山市參觀考察。上午至廿八都,下午到戴氏故里及仙霞關等處。幾處雖皆曩日嚮往未至之地,今卻了無興致,本來想攜帶洞簫去仙霞嶺一弄,亦沒了念頭,心中掩不住陣陣悲痛,眼淚幾度欲出,腦海中總浮現王先生的音容笑貌。一天之中,風雨陣陣,松竹低首,亦仿佛為先生而傷悲垂淚。值此情景,對先生之情感,很想訴諸筆端,奈何總無法坐定。
五月一日飛深圳航班,原定十二時起飛。十時許趕至衢州機場,卻又遇航班延誤,近十六時纔起飛,抵達深圳已是晚上,不禁身心俱疲。二日晨起,但見悼念先生信息滿圈滿網,打開電腦,卻又不知從何說起,唯有略敘先生教導之恩,以表哀思!
初 見
作為江蘇豐縣人,很早就聽說先生是同鄉,每每拜讀先生著作,使用先生所編工具書,無不仰思仰慕,但直到一九九九年,纔得與先生見面。這一機緣,卻是得王雲海先生(1924–2001)促成。
王雲海先生是江蘇沛縣人。因漢高祖劉邦是沛縣豐邑中陽里人,稱帝後將豐邑置為豐縣,故自有漢以後,豐、沛二縣關係就非常密切,有「豐沛不分家」之說,所以豐、沛兩縣人見面格外親近。一九九五年,王雲海先生赴臺參加國際宋史研討會,便是受王德毅先生之邀。其間,兩位先生得敘鄉誼,交情日篤,每每笑稱兩人有三同,即同鄉、同宗、同專業。次年,家齊隨業師徐絜民先生赴昆明參加第七屆宋史研究會年會,得瞻王雲海先生面。先生見家齊是豐縣人,又習宋史,格外親切,呵護有加。先生返回開封後,不僅便將自己所有著作及手頭所餘宋史論著寄下,還寫信向王德毅先生介紹了家齊,並將家齊之博士學位論文推薦給河南大學出版社「宋代研究叢書」第三輯出版。家齊在徐州工作時,先生又曾自開封到徐參加同學會,家齊有幸侍奉兩日,聆聽教誨。
一九九九年九月,王德毅先生和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兼董事長高本釗先生(豐縣人)等訪問團來到徐州師大,向學校圖書館捐贈新文豐出版書籍四千餘冊。此次應是先生第一次回鄉。王雲海先生提早便將此消息來信示知。王德毅先生一行到來的當天下午,家齊就在校門內等候。因之前見過照片,王先生一下車,家齊便認出,上前施禮拜見。因有王雲海先生介紹,先生已早知道家齊,見面格外親切。令人驚訝的是,先生離家半個世紀,居然鄉音未改。握手後,先生便介紹旁邊的師母。記得當時情景,家齊上前稱「師母好」,師母謙虛說「不敢當」,先生笑著說:「論輩分,叫師母也是應該的。」王先生又將家齊引薦給高本釗先生。寒暄之後,家齊便隨訪問團到圖書館會議室,參加了短暫的贈書儀式和座談會。因此次先生一行全由官方安排,家齊未能與先生久聚。
手 書
初次見面時,家齊便將幾篇習作複印件呈給先生,請先生指教。十月底,即收到先生手書。先生手書,一依傳統格式,不僅是豎排文字,而且其中平闕格式相當嚴謹,遇自稱,則將己名小字右出。開頭始稱「家齊博士鄉友」,後一律稱「家齊鄉賢契」,令人倍感親切。家齊自幼所受教育,寫信衹會簡體橫排,稱呼格式亦從當下簡易。但給先生覆函,卻覺不宜如此。於是便研習傳統書信格式,不僅繁體豎寫,而且亦以「函丈」用於對先生之稱呼,唯平闕格式未能嚴格遵守。因不習慣繁體書寫,遇到冷僻之字,便須翻查字典,以免出錯。不意與先生書信往還數年,竟習慣了繁體書寫。到中大任教後,課上有香港學生,擔心其不能盡識簡體字,亦為讓大陸學生習慣繁體字,便從此將授課板書改為豎排繁體。以後使用PPT課件,亦採用此格式。
先生不太喜歡電子郵件,認為手書往來,得見親筆書寫,纔令人感到親切,所以家齊曾與先生保持多年的手書通信。先生每有教導,皆以手書示下,家齊亦必恭敬回覆。家齊亦常以手書向先生求教,而先生亦是迅速覆函,十餘年間數達七十餘封。先生每次來大陸,都會事先來函示知。家齊都盡可能趕去與先生相見。記得與先生第二次見面是二○○○年五月在杭州,當時家齊已在浙大古籍所做博士後,奉先生手書告知將到上海圖書館參加族譜學會議(「邁入新世紀中國族譜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安排到杭州觀光遊覽,約家齊一見,並告知聯繫人電話。家齊回信後,便依約定時間在浙江圖書館新館等候先生和師母。近午時,先生、師母一行抵達浙江圖書館,一見面,先生便親切擁抱。家齊當時對擁抱還不習慣,在先生的感召下,亦不自覺伸出了雙臂。家齊將王先生到來的消息告知了業師龔延明先生,龔先生當晚便在樓外樓宴請了王先生和師母,並合影留念。
人類的生活方式最終總是抗不過科技的發展,很多傳統都因科技的發展而改變,手書便是其中之一。大概從二○一五年以後,與先生的手書就漸少了,也是因為先生年事已高,寫手書有時會累,而師母亦建議用電子郵件。之後,與先生聯繫,多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了。儘管與先生手書往來少了,但聯繫卻並未減少,而且或大陸或臺灣,二○一九年以前基本上每年都能見面。雖然不再寫手書了,但多年手書和到郵局寄信的經歷,讓家齊一直能夠記住先生的住址,隨口就能說出:「臺北縣(後改為新北市)永和市(後改為永和區)永貞路○巷○弄○號○樓」。
贈 書
先生不僅每次來大陸必以書籍相贈,而且還一次次郵寄書籍給家齊。最初所贈乃先生自己之著作,先後有《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總目》(增訂版)、《宋史研究論集》(第一輯)、《宋史研究論集》(第二輯)、《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洪邁年譜》、《王國維年譜》、《宋會要輯稿人名索引》、《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六冊)、《姚從吾先生年譜》,以及論文抽印本多冊;繼而便是《宋史研究集》、《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臺大歷史學報》(近二十冊)、《臺大文史哲學報》、《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東吳歷史學報》、《史繹》、《史原》、《明代研究》、《豐縣文獻》等諸多刊物,另有《朱子研究書目新編1900–2002》、《新文豐圖書解說目錄》、《勞貞一先生百歲冥誕紀念論文集》、《宋學探微》(上下冊)、《宋代社會與法律──《名公書判清明集》討論》、《走向南方──唐宋之際自北向南的移民與其影響》、《方杰人院士蒙席哀思錄》、《宋史教學研討會論文集》和《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等。特別是「宋史座談會」結集出版之《宋史研究集》前面多冊,不僅大陸無法買到,臺灣亦不多見,先生每次來,或一冊,或兩冊,陸續帶給家齊,最後雖未得全帙,卻已達十餘冊之多。
先生不僅贈送手邊所有,還經常問家齊需要何書。家齊本不想給先生增添麻煩,但有一次因請韓桂華教授代購嚴耕望先生大著《唐代交通圖考》,不意先生得知,即刻將五大冊買了寄來,而且強調是贈送。家齊收到後,感動之外,更多過意不去。二十多年中,先生贈送家齊的書籍已難以數清,大致估來,應有近百冊。每看到先生之贈書,不禁想起先生和師母來大陸開會之情景,兩個大的旅行箱,裝得滿滿,最多的就是書,另外還有高粱酒等。除贈書外,先生亦送了家齊不少高粱酒和高山茶。
教 澤
二○○六年八月,「國際宋史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二屆年會」在上海舉行,先生和師母又來參會,這是先生繼保定「國際宋史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九屆年會」(2000年)後,又一次參加宋史年會。此次家齊與先生相聚數日,開會之後,一起去南潯參觀,又從南潯轉赴紹興,然後又同去杭州。同行者還有嘉義大學的劉馨珺老師和中大博士生楊芹(今為廣東社科院副研究員)。記得與會學者一同乘大巴前往南潯的路上,程民生老師見家齊與王先生關係甚親密,半開玩笑地說:「怪不得家齊近年學問大有提升,原來一直有高人指點啊!」程老師其實所言非虛,自從家齊與先生相識,先生便將家齊視為自己的學生,耳提面命之外,便是贈書教導、手書點撥。先生手書中,大多都是關於學術之事,教導家齊多讀宋人文集、筆記、類書、地志,研究範圍寬一點,多留心海內外學者之相關著作等。另外,還不斷提供歷練機會。
二○○五年九月,廈門大學舉辦了紀念科舉制廢除一百年的「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先生自然在被邀請之列。大約是當年初,先生寫信給家齊,告知九月將去廈門參會,鼓勵家齊亦去參加,順便相聚。為與先生見面,家齊便向會議主辦者劉海峰教授致函,打著王先生旗號要求參會。劉老師非常熱情,很快發來會議邀請函。但家齊之前從未研究過科舉問題,不知寫何文章參會。為此多日縈繞在懷,最後決定先研讀有關唐宋科舉論著,尋找可供撰文的題目,經過半年的研讀,終於結合《北宋名臣余靖》一書之撰寫,發現了書判拔萃問題,寫出〈宋代書判拔萃科考〉作為參會論文。會上,該文不僅得到先生的認可,還得到業師龔延明先生和科舉研究專家李弘祺先生的肯定。自此,家齊亦拓寬了學術視野,開啟了對宋代選舉制度的研究興趣,之後又陸續撰寫出多篇研究論文。
二○○六年,家齊在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宋史研究叢稿》一書。此書便是王先生推薦給高本釗先生,並審校、作序。其間,先生對文稿存在的問題一一指出,特別就史料徵引規範和解讀問題,提出不少指導性意見,令家齊獲益匪淺,對治學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領悟,以後每遇古籍版本及史料釋讀問題,皆不自覺地多了幾分警惕,慎之又慎。
二○一一年四月,家齊赴中國文化大學參加第二屆「海峽兩岸宋代社會文化研討會」,這也是家齊第一次去臺灣。先生甚是高興,會議結束後,便讓家齊去家裡住。家齊進到先生家中,第一次見到學者家中藏書之豐富,真是歎為觀止。先生的家是兩套兩居室公寓房打通相連,無論客廳、臥室,凡有空處,皆是擺滿各種書籍的書架。有一專門放書的房間,卻是書架縱橫多排,如圖書館之藏書室,一排排書架間僅能容身。先生的藏書,據劉馨珺老師稱,多達兩、三萬冊。其中最讓家齊驚歎的是,有一書架,密集排列著大量日文書籍,抽出來看,上面多有簽名,或是宮崎市定贈送,或是青山定雄贈送,或是周藤吉之贈送,這是家齊連想都想不到的,在大陸更是未曾見到。先生不僅介紹家中藏書,還不時抽出其中一冊打開來,給家齊講解其中的學術問題。二○一二年二月至四月,家齊受楊宇勛教授之邀,有幸到中正大學客座兩月。其間又到成功大學、暨南國際大學、清華大學、東海大學、淡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和建國科技大學訪問。先生不僅囑託在臺同道多方關照,還趁家齊到臺北之機,帶領家齊參觀了臺大圖書館和歷史學系,並安排家齊在宋史座談會上作學術報告,地點在臺師大。晚餐之後,先生又讓去家中住宿。到家之後,先生仍如上次一樣,拿出一本又一本藏書,講解其中重要之內容,直至深夜。
以往拜讀先生之著作,聽先生講學,每感先生學問之深厚。知先生學問以人物年譜為基,既有舊學堅實之功,又善於把握學術前沿問題,將傳統與現代有機結合,闡揚宋人正氣,發軔不少新的議題,尤對人物與家族問題最有建樹。其〈宋代賢良方正科考〉發表於三十二歲時,堪稱史學研究範文;《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則在數十年前便引導新潮;《李燾父子年譜》、《洪邁年譜》、《王國維年譜》等乃人物研究之經典;《宋會要輯稿人名索引》、《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等工具書,更是嘉惠學林,被眾多學者置於案頭,作為必備。但家齊進入先生家中,得先生耳提面命之後,便覺以往認識之膚淺。當時便有一種感覺,先生學問之博大精深,與乾嘉諸儒相比,亦不遑多讓。
先生瀏覽新刊學術論著,常發現其中史料斷句和釋讀之誤,不少論著作者是當今學術名家。凡遇此事,先生或以全篇,或手錄、複印局部以示家齊,點點滴滴,無不令家齊深沐教澤。
鄉 情
先生出生於豐縣王莊,今屬豐縣歡口鎮。先生曾在家鄉附近的山東地區讀書數年,十五歲時輾轉南遷,次年離開大陸,先後在澎湖和員林(彰化)讀完中學,後考入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一九五九年畢業後,在「中央圖書館」工作四年,於一九六三年返回母系任教,再回故鄉,已是離家五十一年後事。聽先生說,剛到臺灣那些年,因思念父母,常常流淚。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三年,雙親先後過世,先生皆未能回家守喪,想來令人傷悲。
先生對家鄉之情深,非常人可比。看先生著作,文後署名多是「豐縣王德毅」五字,這是效仿南宋王應麟(1223–1296)為文皆署名「浚儀王應麟」之典式,意即雖播遷在外,仍銘記家鄉。先生多次向家齊講起王應麟事。聽先生說,第一次返鄉探親時,家鄉仍很落後,起居皆無法適應。但王先生對家鄉並無厭棄,而是時刻關心家鄉的發展,盼望家鄉人生活不斷改善,特別是希望家鄉的教育能不斷興旺。臺北有豐縣同鄉會,不斷募集資金捐贈故鄉,資助家庭貧困的學生讀書;還辦有期刊《豐縣文獻》,其中有「豐人行誼」、「縣事鉤沉」、「鄉邦錦繡」、「學術探討」和「小品精粹」等欄目,每期的審讀編校工作,都主要是先生承擔。家齊每次返回故鄉,都會把所見故鄉的新貌向先生匯報,先生見信後,無不表示欣悅。
先生很想讓家齊去趟臺灣,二○○○年時,先生曾說要請臺北豐縣同鄉集資,作為赴臺旅費,邀請家齊去臺灣參加漢文化研討會。家齊不想太勞煩先生和在臺家鄉前輩,沒有同意。二○○四年,家齊想出版《宋史研究叢稿》,先生欣然幫忙,不僅和新文豐出版公司談定出版事宜,還把全書審校一遍,並為作序。雖是一本小書,但作者、序者和出版者俱是豐縣人,成為家齊心中永久的紀念。二○一一年,家齊首次赴臺,先生便讓家齊到家中住宿,晚上給家齊講解學問至子時。次日晨,又和師母一起,帶家齊去附近有名的永和豆漿店品嘗美味早餐,然後帶領家齊去了新文豐出版公司,拜見高本釗先生,參觀了新文豐的書庫。在和高先生敘談時,見先生不斷打瞌睡,後來一問,先生告知,昨晚家齊安歇後,又繼續看書至凌晨兩點。高先生與王先生一樣,亦是十餘歲離家來到臺灣,同樣是故鄉情深。知家齊即將返回大陸,便令長子道鵬去旁邊店裡,買來有名的肉脯相贈,中午又預訂午宴,請來多位豐縣同鄉相聚,座中同鄉多逾古稀之年。次日,家齊離臺返穗,王先生又執意相送,陪家齊乘公交至一車站,看著家齊登上去桃園機場的大巴。先生時年七十有八,行動已略有遲緩,眼望車外的先生,家齊心中多有不忍,牽掛著先生回去的路程。
先生見豐縣人就格外親切。有一次先生來信說,看到南京大學中文系鞏本棟教授到臺灣大學訪問的信息,消息上寫明鞏教授是豐縣人,令人高興。感先生此情,家齊便從網上找到鞏教授的郵箱,寫信告知王先生濃濃之鄉情。後來鞏教授再去臺灣,便和先生聯繫,見面數次,先生在臺大附近那家常去的飯店宴請了鞏教授。因此之故,家齊亦和鞏教授建立聯繫,不僅互通郵件,還相互贈書,衹是事隔數年後,纔在廣州見面。
在先生心中,家鄉情誼是至上的,而與家齊之間的親密關係,亦是同事和朋友們皆知和贊賞的。二○○八年三月,由家齊操辦,在廣州舉行「宋史研究新視野學術研討會」,當時計劃邀請的學者主要是中青年。時任中大人文學院院長的陳春聲教授和歷史學系主任劉志偉教授便建議家齊特邀王先生前來,先生欣然接受邀請,蒞臨中山大學。二○一六年八月,家齊又承辦「十至十三世紀中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七屆年會」。先生時年已八十有三,當家齊向先生發出邀請時,先生毫不猶豫地說:「家齊辦會,我一定得去。」先生不僅和師母同來,還動員了不少臺灣學者前來參會。會後,有去陽江參觀「南海一號」沉船之安排,家齊因會務纏身,未能陪同。先生在海絲博物館購得古船模型一件,回來送給家齊,家齊至今保存。
先生平日生活儉樸,但對家中親朋卻是傾力相助。先生兄弟共四人,長兄德宏,亦在臺灣;兩位弟弟,一名德勛,一名德池。自一九七九年起,先生便從美國往家寫信寄錢,兩岸能通信後,更是頻繁。一九八八年八月,始得約兩位弟弟在香港見面。先生十分關心弟弟子女的成長與教育,幾位侄子、姪女名字,多為先生所取,與自己三個兒子一樣,名字中間皆用家譜中「繼」字行輩,侄子末字均取「王」旁之字,姪女末字取「艹」頭字。先生知道在家上學皆須用錢,仍不斷往家匯款。侄子、姪女結婚,先生亦皆給予資助。因同鄉之故,家齊多次充當中間人,或代為聯絡,或代為匯款。每次匯款,或七、八千,或上萬(人民幣)。印象中,先生給家裡寄錢,持續到二○一一年以後。
兩 岸
先生愛家鄉,更愛國,一心盼望實現兩岸統一。先生平時不議人非,唯對不利兩岸關係之人與事表示憤慨。然先生衹是一學人,於政治無能為力,衹有多方促進兩岸學術交流。先生曾於一九九一年八月赴北京參加第二屆國際宋史研討會,一九九七年二月,又到浙江蕭山參加《王國維全集》編纂會議。自二○○○年在河北大學召開的「國際宋史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九屆年會」起,先生便經常來大陸參加學術會議,家齊見到先生參加的,除宋史年會外,還有「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南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和「海峽兩岸宋代社會文化研討會」等。每次學術會議,先生都作為臺灣地區的代表發言,或介紹臺灣宋史研究狀況,或發表最新研究成果,或表達進一步加強兩岸學術交流的願望,殷殷之情,每令人感動。
自二○○九年起,兩岸之間開始舉辦兩年一次的「海峽兩岸宋代社會文化研討會」。研討會最初雖由浙江大學和中國文化大學輪流舉辦,後來河南大學和雲南大學亦加入主辦行列,但先生無疑是重要推動者。二○一九年以前的六屆海峽兩岸會議,先生每次都參加。二○一九年雲南大學主辦的海峽兩岸宋史會,先生時年已是八十有六,仍和師母一起前來參加。
先生與大陸學者的交往更是廣泛,無論是老一輩如陳樂素(1902–1990)、鄧廣銘(1907–1998)、徐規(1920–2010)、漆俠(1923–2001)、王雲海(1924–2001)諸先生,還是中間輩如朱瑞熙、龔延明、張希清、張其凡(1949–2016)、鄧小南、包偉民、程民生、李華瑞諸先生,先生都有密切交往。對年輕一輩,先生更是視同自己的學生,或贈書示教,或寫信開導。因此,大陸各年輩學者見到先生都很親切、敬重。
思 念
先生將家齊視作學生,亦如同親人,故家齊與先生感情深厚,兩岸相隔,時常想念。以往每年都有數封手書往還,後來則是隔段時間打個電話,熱切盼望能夠多見面。故每與先生見面,家齊都盡可能多與先生相處些時間,一起用餐,一起散步,陪同參觀,說家鄉話。二○一八年八月,先生和師母又赴蘭州參加「十至十三世紀西北史地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八屆年會」,家齊與先生相約早到一天。當時杭州亦在舉行南宋史研討會,家齊便從杭州直飛蘭州,與先生相聚。開會前一天,家齊陪先生和師母一起參觀了甘肅省博物館等處,特別是專程去看了蘭州黃河鐵橋。三人站在鐵橋上,望著滿河奔湧的黃水,東去源源不斷,都無比感慨。記得先生說道:「終於見到黃河了!」傍晚,由家齊在蘭州的兩位本家叔叔做東,宴請了王先生和師母,吃的是北京菜。
次年七月,雲南大學舉辦「第六屆海峽兩岸宋代社會文化研討會」,先生和師母又來參加,家齊亦前往與先生相見。會後,先生與其他學者一行去大理等地參觀,家齊因有公務,沒能陪同,而返回廣州,卻不意昆明一見,竟然是與先生最後一面。二○二○年,新冠疫情肆虐,先生卻中風住進醫院,連親友探視都困難重重,而先生已然口不能言。家齊亦唯有打電話給師母,探問先生狀況。疫情過去後,家齊很想去臺北探望先生,可兩岸關係卻不如以往,大陸人進入臺灣甚是艱難,幾度嘗試,皆不成功。如今驚聞先生仙逝,卻又是空有傷悲,而不能前往靈前弔唁,唯有望海興歎,再興歎!感慨至此,又不免慶幸,先生這幾年雖臥病在床,不聞外面之事,卻亦獨得安寧,不然,知道兩岸狀況如此,該有多傷心啊!
先生之德,堪比昆侖;先生之學,仰之彌高;先生之教,澤被內外;先生之逝,遐邇同悲!半個多月來,南國風雨如晦,或急或徐,如慨如嘆,如泣如訴,仿佛預言著一個世代的結束,哭訴著一位學術巨子的隕落,然先生如楷如模之恩德,豈能訴得盡啊!
二○二四年五月五日於廣州
附記:拙文於五月四日完成初稿後,送呈多位師友指謬,蒙黃寬重、劉靜貞、王瑞來、鞏本棟、苗書梅、范立舟、吳雅婷、李丹婕及王先生侄子王繼琮等諸位先生提供準確資料並校正誤字,謹致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