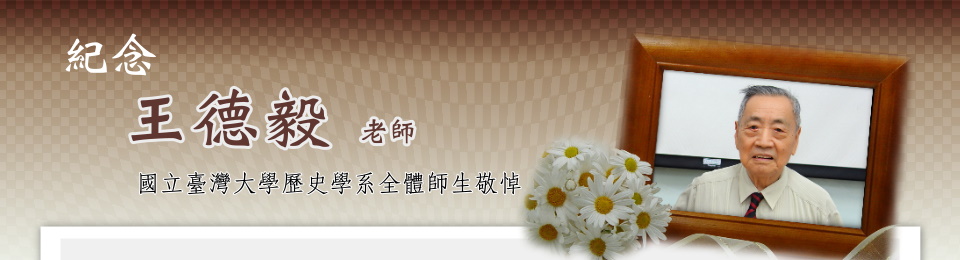| |
「怡然敬父執」——悼德毅教授
王瑞來
(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
|
人間四月天,按農曆還是暮春三月,江南鶯飛草長,陽光明媚。值此之際,瑞來到趙抃的家鄉衢州,參加小書《大宋名臣趙抃》的新書發佈會。其間與友人登藥王山,訪天生石樑樵夫爛柯處,發思古幽情,想先賢懿行。其樂融融,恰如這滿眼新綠的季節。不過,這一切,在一天早上蒙上了陰翳。那天早上,手機傳來黃寬重先生的微信:「剛才得知我的老師王德毅教授於二十九日晚上九時二十三分辭世。」接到微信,心情驟然變得沉重。此後的天氣也是陰晴不定,時時大哭,返程從衢州前往寧波機場,一路大雨,我心同哭,飛機亦推遲起飛。近一年來,臺灣大學名譽教授王德毅教授臥病的訊息從不同管道常常傳來。但我一直相信吉人天佑,內心裡祈禱德毅教授早日康復,未曾料到,竟會這樣快地離去。
瑞來與德毅教授有著將近四十年的交往,這是持續了一生的友誼。早在海峽兩岸資訊溝通與人員往來尚不順暢的上個世紀80年代,我的《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出版後,曾拜託在杭州國際宋史研討會相識的李弘祺先生輾轉郵寄給德毅教授一套。當時李弘祺先生執教香港,因赧然相托。之所以將書贈送給素昧平生的德毅教授,是緣於我在撰寫之際拜讀了德毅教授寫在《宋史資料萃編》第二集的〈宋宰輔編年錄題端〉的研究,除了接受德毅教授的觀點之外,也稍有不同的認識,因此想向德毅教授求教。幾個月後,同樣是通過李弘祺先生轉寄,我收到了德毅教授《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李燾父子年譜》等數種大著。這次往復贈書,便成為我與德毅教授交往的開始。
在未曾實際接觸的交往中,其實還有一件令德毅教授不快的事情。同樣是在1985年杭州國際宋史研討會相識的美國戴仁柱教授,到訪北京時,專門給我背來包括索引在內的6大本德毅教授主編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在大數據時代到來之前,這部索引可以說是宋史研究者的至寶。瑞來當時供職於中華書局,擔任負責宋史方面的編輯。那時大陸尚未加入版權協議,所以,經請示之後,便將這部索引翻印,在大陸出版了。儘管《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的大陸版印行嘉惠了學界,但畢竟屬於盜印,沒有跟德毅教授打招呼,也沒有給報酬。後來,在見到德毅教授時,我深懷不安地表示了歉意。
神交十多年,到了寓居東瀛之後,1999年應邀參加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才在臺灣大學第一次見到德毅教授。跟東京大學頗為相似的臺大歷史學系的老式建築中,德毅教授與梁庚堯教授共用一間研究室。當時在研究室中拍攝的合影,珍藏至今。第一次赴臺,在會上會下,椰林大道、傅園、鹿鳴館、易牙居都留下了與德毅教授初見交往的難忘記憶。那次會議,我提交的論文是〈「平世之良相」王旦——君臣關係個案研究〉。後來論文收錄於臺大歷史學系主編的《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之中。德毅教授親自編審了這部論文集。在審閱瑞來的論文時,對王旦父親的名字,我原來記為「祐」,德毅教授特別致信指出應當作「祜」。德毅教授的細緻認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臺大初見之後,便開啟了與德毅教授的頻繁交往。第二年的2000年8月,很快又在保定的第九屆宋史研究會年會暨國際宋史學術研討會上見到了德毅教授。除了開會一起研討,還同遊清西陵。在河北大學至今已經幾乎成為宋史學者朝拜聖地的宋史研究所平房拱門前,與德毅教授以及黃寬重教授的合影,至今還會喚起當年的記憶。
此後的2004年又一同在河南濮陽參加「澶淵之盟」一千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不僅與德毅教授同台發言,留下了珍貴的影像,我在參觀澶淵舊郡拍攝的照片中也有德毅教授的身影。在大學的東洋史授課時,每講到澶淵之盟,都會在PPT播放這張照片,心緒便隨時光穿越到當年,仿佛又置身其境。
時隔一年,2005年便與德毅教授再會於廈門大學的科舉廢除一百年「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那次以會議提交的論文為契機,瑞來明確提出了宋元變革論的議題。這其中也包含了德毅教授的鼓勵。2006年,與德毅教授重逢於滬上,參加第十二屆宋史研究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黃浦江夜遊,眺望東方明珠塔,照片也將那一歡樂的時刻定格。此後2009年、2015年杭州的第一屆、第三屆南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年廣州第十七屆宋史研究會年會暨國際宋史學術研討會以及2016年在臺大召開的「士人與近世社會文化變遷(1100~1500)國際學術研討會」,都頻頻與德毅教授相會。開會有時同處一個討論會場,遇到曾經討論過的共同話題,與德毅教授往往會遙遙相視,會心一笑。
在2013年的3月,承黃寬重教授的邀請,瑞來曾到臺灣訪學一周,在漢學研究中心、臺大、清華、淡江等大學分別做了演講,宣講我倡導的宋元變革論。在梁庚堯教授主持的演講會上,臺大歷史學系的會議室師友濟濟一堂,德毅教授坐在前列的樣子依然歷歷在目。

那次一周小住,德毅教授專門請我吃飯。在日本,學者們開完研究會後,往往習慣到常去的居酒屋聚飲,幾十年如一日。臺灣的學者大概也是如此。前面提到的臺大附近羅斯福路的易牙居,據說就是臺大教授們的定點聚飲之處。德毅教授也是帶我到的這裡,同席的還有張維玲。由於德毅教授的介紹,當時還是博士生的維玲過後還把她的博士論文列印稿送給了我。維玲現已在香港理工大學執教,這本題為《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前兩年在大陸出版,頗得好評。維玲的成就自然與德毅教授指導分不開。回憶起來,那次德毅教授請吃的蘿蔔糕仿佛依然餘香在口。
德毅教授以傳統的方式治學,抄錄有幾十萬張卡片,扎扎實實,十分勤奮,撰寫了大量的著述。他在許多領域開闢草萊,都給後來的學者以極大的啟示與助益。對於這一點,我從自己的學史經歷中便深有體會。十多年前,我曾在《歷史研究》發表有〈范呂解仇公案再探討〉一文。題目中的「再」字,就表明我有所承繼。這一承繼就是德毅教授的〈呂夷簡與范仲淹〉,正是這篇文章,啟發了我的問題意識。
作為老一輩學人,德毅教授的辭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或許有人會認為,德毅教授的治學方式已經過時。在我看來,在大數據時代到來之前,德毅教授,還包括日本的佐伯富、梅原郁等先生編製的大量索引,都為數位化建設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儘管現在擁有各種比較完備的數據庫,但德毅教授等學者編製的索引工具書依然沒有失去其使用價值。這些索引工具書不僅可以直接改造編入數據庫使用,即使是紙本的狀態,在研究時也往往不可或缺。還是訴說我自身的體驗。比如說《宋會要輯稿》,儘管已經有了數位典藏可供自由檢索,但德毅教授編纂的《宋會要輯稿人名索引》和梅原郁先生所編《宋會要輯稿編年索引》,依然是我的案頭必備。
在鄧廣銘、漆俠等老一輩宋史研究的領軍人物去世之後,德毅教授成為海峽兩岸宋史學界的主心骨般的重要存在。每次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臺灣,學術會議上都能聽到德毅教授語重心長的諄諄教誨,讓後生學子受益匪淺。此外,德毅教授還是聯繫國際宋史學界橋梁般的存在,跟美、日等各國的學者保持有廣泛的學術聯繫與友誼。每次見到德毅教授,都讓我代為問候他所熟識的日本學者,還多次請我把他的新著轉贈給斯波義信等先生。
德毅教授為人淳樸忠厚,古道熱腸。從第一次相見,瑞來便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我每每見到德毅教授,如沐春風,有著親情般的感覺。杜甫有句詩,叫「怡然敬父執」,正可以表達我對德毅教授的感情。瑞來的父親年長德毅教授幾歲,早在80年代便已去世。所以,有一次,我對德毅教授脫口以「父執」相稱。德毅教授聽了,笑吟吟地說:「父執好,父執好!」從此,便以父執相稱。在感情上,不止於父執,翻檢在保定遊覽清西陵時的合影,我與德毅教授兩手緊扣,形同父子。正因為這樣,無論於學術,還是於私情,德毅教授的與世長辭,都讓我悲慟難抑,心無所依。我的這種感受並不是個人的。在驚悉德毅教授去世後,我在大陸的大宋史學術交流微信群悼念時說了上述這番話之後,河南大學的苗書梅教授就回應說:「誠如王瑞來先生所言『熱情忠厚,親切如父執』!」可見,這是多數學者的共同感受。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其實,學者無憂。物理的生命雖有竟時,但學術的生命與世長存,學術成就擁有著超越時空的生命力。我們以有限的人生,在人類文化的建設上,從前輩那裡接棒,跑一段接力,再把棒傳給下一代,有限的個體便在文化傳承中獲得了萬壽無疆,這就是我們從事學術活動的意義和使命。德毅教授的道德文章和學術業績為我們樹立了典範。高山仰止,學如積薪,在德毅教授等先輩學者留給我們的學術積累之上,我們需要加倍努力,才能不負所望。
饋贈高山茶猶在,先生已然入仙林。德毅先生研究過范仲淹,移范仲淹在《嚴先生祠堂記》的結尾悼念德毅先生:「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瑞來匆匆寫就於5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