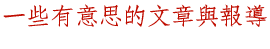
外匯存底世界排名第三不見得是值得驕傲的事。
台灣國中生活的體驗。
2003年5月到6月之間台灣發生 SARS 疫情, 及口罩短缺現象。 我認為口罩短缺是政策管制的結果。
希望你能給我們一點意見。
Law in America,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這本小書很精簡地討論美國法律制度發展的歷史。
雖然是以美國為對象, 但觸類旁通,
若有人想要了解法律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 這本書很有幫助。
比較遺憾的是, 書中未曾討論 law enforcement 的問題。
台灣最近出版了幾本有關於荷蘭統治期之研究, 這些書較冷門, 故值得推廣一下:
1999.9.21地震已屆一年。 一年之後, 我們應該能較冷靜地回顧與檢討。 本文是1999年11月 (?), 我在台大經濟系座談會上的發言。
*************************
地震發生之後一兩天, 國外的專家陸續到台灣來幫忙救災。 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報導, 印象非常深刻, 覺得他們連走路都很專業。 接下來, 新聞媒體報導了他們使用的一些儀器設備, 我有點感嘆說: 「我們的救災通常用兩隻手, 一個是手, 一個是怪手; 但是國外的專家就有一些先進的儀器可用來做救災的工作。」
從各界的救災工作, 可以發現我們的愛心不比國外少。 但救災講究的不是愛心的多少, 而是效率高低。 科學的研究, 包括氣象、地理等, 對於救災的確有幫助。 譬如說, 地質學的知識告訴我們, 全台灣有多少地方在斷層上, 我們現在知道不要在這上面蓋房子。 同樣的, 物理學的知識讓我們製造救災儀器。 這是科學知識的用處。 因此, 經濟學家在討論救災之前, 我們先來思考: 經濟學知識為何與救災有關?
地震發生以後, 災區就開始發放救濟物資。 我們都知道經濟分析的重點就是在討論資源分配的問題。 例如, 超級市場裡面的商品透過什麼樣的方法, 賣給各個消費者? 這是一個資源分配的問題。 經濟學告訴我們, 資源分配方法各式各樣, 其中之一叫做市場機能, 也叫做價格機能。 每樣商品有它的價格, 如果所得夠多, 而且你認為商品的價格適當的話, 你就去買。 市場經濟社會就是透過這種方式, 把所有生產的物資分配到各個家庭裡去。 我們說這是透過市場機制分配資源。
這個方法看來簡單, 不過經濟學家的研究發現, 透過價格機制從事資源分配是最有 「效率」 的方法。 這是經濟學家所告訴我們的。 但是, 這個知識有用嗎? 它可以像地質學、 物理學一樣, 在救災工作中發揮實際的幫助嗎?
回到災區現場, 我們面對的問題是物資怎麼分配到災民手中。 我們所看到實際的物資分配方法中, 並無價格機能。 在災區, 災民可以免費領取物資, 價格為零。 因為價格是零, 所以救災單位設計一個辦法來發放物資; 誰要領取物資, 就必須來排隊。 因此, 我們採取排隊的方法來作資源分配。 但是, 排隊是分配物資的好方法嗎? 從各種報導來看, 這種方法顯然問題很多。 譬如, 有些家庭全家出動, 重覆領取; 有些人非得要全新的棉被不可。
如果我們能以價格機制來分配物資, 以上的問題不會出現。 在價格機制下, 每樣物資有其價格。 你要不要這項物資要看你所得有多少, 看物品價格的高低, 還看你的需求如何。 因此, 在災區如果使用價格機制來分配物資, 第一步是將每樣送來災區的物品標上價格, 再出售給災民。
很多人可能覺得這個方法蠻冷酷的, 災民已夠可憐了, 還要他們花錢來買救濟物資。 不過, 以上我只講了辦法的前半部分。 物資賣出之後, 救災單位再把全部收入移轉給各受災家庭。 後半部分的工作事實上是最困難的; 今天報紙上所描述的種種問題, 絕大部分都與此有關。 不過, 先不談後半部分, 如果以價格機制來分配物資的話, 它會比以排隊來領取物資的方式更有效率。 因此, 適當的運用經濟學家的知識對於救災工作是有幫助的。
接下來, 我想談毛老師剛提到的一點, 政府在救災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救災工作的前三天, 重點是把受困人員救出來; 這一部份我想與經濟學沒什麼關係; 但是, 之後的復建工作則與公共政策有密切關係。 換言之, 復建階段的工作與政府有關。
經濟學對於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有很多討論, 也得到幾個重要的結論。 簡單來說, 若是一般性的商品, 由民間部門從事生產與分配, 效率最佳。 政府介入反而降低效率。 在台灣, 我們對此感受最深。 不過, 在某些情況下, 政府有其重要角色。 第一、 若商品具有外部性 (externalities), 市場機制不能有效率的解決生產與分配的問題, 政府或許應介入。 第二、 若商品具公共財 (public goods) 特性, 政府可能也須介入。
要討論災後重建工作, 外部性與公共財是討論的起點。 從這個角度來看, 政府絕對有它應該做的事情, 例如, 中橫公路毀損非常嚴重, 整個台中地區的供水系統也受創, 公路與供水系統一般認為具有公共財的特性, 政府絕對需要花錢花精神來作修復工作。
不過, 從報紙上的報導, 我感覺政府工作的重點並不在此。 報紙裡所討論爭執的是: 災民要發給50萬? 還是100萬? 還是200萬? 發放救濟金是財富重分配, 和我們剛剛所說的外部性與公共財毫無關係。 財富重分配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但是, 財富重分配通常透過立法的程序。 譬如, 所得稅制內就有財富重分配的機制; 社會福利制度也有財富重分配的機制。
現在發生地震之後, 政府花了很多時間跟精力在做財富重分配。 這是當務之急嗎? 我們之所以要問這個問題, 原因是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 如果它花了很多力氣在做財富重分配, 它就沒有多少力氣從事基礎建設的修復工作。 事實上, 台灣的經濟制度已內含一些財富重分配的機制。 如果你的所得下降, 其他人會提供一些幫助。 譬如, 我們的所得稅是累進稅率。 今天台中、南投地區的災民不幸因為地震, 財產遭受損失, 所得下降; 他們明年所繳的稅會比今年少一點。 由此可見, 我們的制度本來就有財富重分配的機制。 那麼, 在發生地震時我們又特別花力氣作財富重分配, 那是不是表示我們原來的制度並不理想, 無法處理這種特別的狀況?
如果真的是如此, 那我們的問題是在制度層面。 解決問題的辦應該是透過立法, 修改制度, 而不是靠行政首長跟災民之間的討價還價, 決定財富重分配的額度。 根據報導, 李登輝總統在10月19日到埔里地區, 跟災民保證 「申貸的權益不會受損」。 我覺得這是很糟糕的講法。 我們今天到銀行借款, 沒有權益不權益的問題。 借貸行為是市場的自由交易。 如果我的信用較差, 銀行也可以借我錢, 但利率可能是百分之二十。 你的信用較好, 同樣去借錢, 利率可能是百分之五。 在市場機能下, 你有什麼樣的條件, 就會面對什麼樣的利率。
現在, 有人受到地震災害, 突然之間他就有一些特別的權益。 譬如, 他的利率本來是百分之十, 現在突然變成百分之三。 問題是, 如果此人獲得特別權益的話, 意思就是社會上其他的人有特別的義務。 某人到銀行借錢, 利率是百分之十。 今天因為地震的關係, 政府規定他可以用百分之三的利率借到錢; 它的真正意思是說, 百分之七的利率強制要由其他的人來補貼。 我們的社會若變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是很遭糕的。
我們看到災民上總統府請求。 我也同情災民, 但是他們所作的某些請求是不對的。 有些災民覺得他受到損害的時候, 覺得這個社會欠他一筆; 其他人有義務要恢復他原有的財產。 表面上看來, 這個社會多麼美好! 但如果我們的社會真的變成這個樣子, 問題就嚴重了。
將一般人民所納稅款移轉給社會上最有錢的家族, 這是什麼樣的政策?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這筆低利貸款間接補貼了各飯店的住宿者。 會選擇這些較高級飯店的住宿者, 一般而言應為社會上中高收入者。 將一般人民所納稅款移轉給社會上的中高收入者, 我們需要這樣的政策嗎?
地震之後一個星期, 教育部於1999.9.28下令給各學校, 「賑災款請各主辦會計人員, 向機關首長陳報應彙繳至行政院賑災統籌專戶」。 我不曉得其中道理何在? 行政院在賑災行動上比較有效率嗎? 老實說, 我看不出來。 現在講來是放馬後砲, 不過, 未來再有捐款行動時, 我們首先應思考: 要捐給誰? 之後, 再把錢拿出去。
事實上, 我們應該能透過價格機能發放救災物資。 辦法如下: 將所有各界捐贈之物資以正常價格在災區出售, 所得之收入再依各受家戶受災嚴重程度發放救濟金。 如果某些捐贈物資數量太多, 我們也可以拿到災區外出售, 所得款項再發放給災民。 此一辦法的重點是: 物資之發放仍透過價格機能, 故可避免目前所看到的許多問題。 (當然, 一個最困難的問題仍無法避免: 如何認定受災戶?)
第一個階段是地震發生之後72小時內的緊急救災階段。 以9.21地震的規模而論, 地方政府本身也是 「災民」, 由本身是災民的地方政府來救濟災民, 我們不可能期望太多。 事實上, 我們發現救災行動必須動用的某些資源, 如直升機與軍隊等, 只有中央政府才擁有。 不幸的是, 地震發生的好幾天之後, 我們才看到中央政府成立所謂的 「督導中心」。 這緊急救災階段的救災行動明明是行政院長該作的事, 為什麼變成是副總統出來 「督導」 呢?
第一階段的政府行動應該或許可以從保險 (insurance) 的角度來了解。 台灣各家庭/企業每年繳給財政部的稅款中, 有一部分是保險費。 一旦某地區發生災難事件, 政府即將所收之保險金用於災區。 但即使是保險, 我們仍有下一個問題: 為何此項保險須由政府來作? 民間來作保險效率不會比較高嗎? (我個人不很清楚問題的答案是什麼?)
賑災的第二個階段是災後重建階。 這個階段, 政府應該作什麼事呢? 根據報紙報導, 救濟金的發放也產生種種問題。 發放救濟金給災民是財富重分配: 將災區外居民的財富重分配一些給災民。 我相信民間賑災機構在這方面的效率絕對高於政府部門。 因此, 我看不出來政府為何要從事類似的工作。
事實上,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思考: 為何要作財富重分配? 台灣各地每天都有種種的天災人禍。 有人發生車禍, 有人發生火災, 有人突然得了重病。 這些不幸的人散居全國各地, 人數其實也不少, 但他們所得到的 「救濟金」, 相較之下顯然少太多了。 9.21地震的規模大很多, 但只是因為受災規模大, 我們就必須作特別的財富重分配?
若報紙報導屬實, 有些災民甚至覺得政府發放救濟金是天經地義的。 不過, 且讓我們思考一下救濟金的財源。 救濟金的主要來源是人民所繳之稅。 如果領取救濟金是 「權利」, 那等於是說 「強制性的財富重分配」 是天經地義之事。 這樣子的想法與作法若變成常態, 這個社會的問題就嚴重了。 萬一我今天在路上不小心跌倒, 我也要求政府發放救濟金。 (亦即要求別人來救濟我。) 某人今天不幸發生火災, 他也要求發放救濟金。 我看不出來這是好的制度。
但是, 迄今為止, 我還沒看到任何政府官員就此問題清楚表達意見; 我倒是看到高層官員自認為救災效率高, 因為發放高額救濟金甚有效率。
經濟學的分析告訴我們: 政府的經濟功能是在於外部性與公共財上。 9.21地震之後, 許多的政府救災行動和 「外部性」 與 「公共財」 一點關係也沾不上。 政府如果將大部分的資源用在不該用的地方, 真正該作的事情當然也作不好。 這是行政效率好壞的關鍵所在。
怎麼辦呢? 台北市居民應該有強烈的感受: 在台北市長由人民選舉, 並且輪換之後, 台北市的行政效率比起以往高了許多。 這就是民主政治的力量, 每人珍惜自己的選票, 讓真正的政黨輪流執政出現, 我們就可能替自己創造福利! 另一個問題是: 「有什麼樣的人民, 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人民如果不能好好思考我們所面對的問題, 對於政府的行動沒有清楚的了解, 政府官員們也就可以胡作非為。
明年三月的總統選舉, 請珍惜你的一票!
我知道這兩個軟體的市場占有率很高, 我自己也使用了其中一項軟體。 但是普通經濟學教科書都告訴我們, 獨占有損效率。 教育部的作法是加強 Microsoft 的獨占, 這有道理嗎? 事實上, Excel 有許多替代品, 如 Lotus 試算表; Word 也有許多替代品, 如 Word Perfect, TEX 等等。 另外, 許多理工科研究人員所使用的工作站, 不一定採用 Microsoft 軟體。教育部指定使用 Microsoft 軟體, 這是不是圖利特定廠商呢?
另外一個 (也許是更重要的) 問題: 看看各單位依教育部格式所打出的申請表, 我感覺版面之品質比以往不用電腦排版時更差。 所謂 「排版品質差」, 意思是更難閱讀。
記得在美國讀學位時, 電腦排版尚未普及, 學位論文或研究成果皆以打字機打出。 每一個學校都會規定論文格式, 其內容是: 行寬、字體大小、行距等等; 另外, 各校也會規定圖表陳列方式、參考文獻之格式等等。 這些才是真正影響容易閱讀與否的因素。 現在, 許多政府單位只要求使用某項軟體, 排版品質似乎沒有人關心。 現代科技真的代表進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