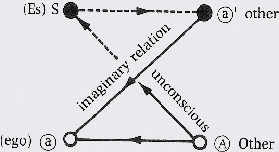|
在武俠小說所呈現的陽剛世界中,女性角色所被分派的「任務」一直頗為固定,也就是為男主角在忠孝節義、武林恩怨的情節之外勾勒另一條愛恨情仇的支線,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女性角色也就難免被類型化,她們的存在意義往往是依附在男性角色身上的,而所言所行也常常是為了爭取男性的鍾情;本論文雖然也是從一個看來相當女性主義的詰問—「他不看她時她在嗎?」—出發來研究《天龍八部》中段正淳身邊的女性,但要申述的卻不是金庸小說如何牴觸了女性主義的訴求。雖然如果我們要列舉金庸小說中願意為男主角生、為男主角死的女性角色,可以舉出不少的例子,但一來金庸小說所形塑的女性角色類型變化其實頗多,以某些例子來斷定金庸對女角的刻畫出自父權中心主義並不甚公允,二來這樣的批評實在屢見不鮮,以至於似乎具有女性主義的意識便無法享受閱讀金庸小說的樂趣,本論文因此希望跳出將武俠小說看成女性主義者要誓師討伐的讀(毒)物這樣的傳統,藉由檢視小說中負面的女性角色其觀看/認同的方式,積極地釐清:金庸筆下某些負面形象的女性角色她們的認同模式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以至於陷溺在依附男性而生的處境中難以自拔?透過精神分析的閱讀方式,有沒有另一種有別於這些女子所採取的觀看方式,可以將(女性)主體自愛慾情仇的狹隘空間中釋放出來? 「他不看她時她在嗎?」這樣的一個問題其實是挪用拉岡(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思考所發出的詰問。在科學界,Bohr提出量子力學此一學說,認為一個物理量只有在當它被測量之後才是實在的,之後,持反對觀點的Einstein表示,一個嚴謹的物理理論應該要區別「客觀實體」以及這個理論運作的觀點,客觀實體應獨立於理論而存在;Einstein問道:「難道月亮只有在我看她的時候才存在嗎?」拉岡的精神分析傾向接受量子力學提出的反省,肯定了主體的觀看與否及觀看方式在在影響到他所看到的結果,如此一來,「我不看月亮的時候,她就形同不在」便不再是荒謬絕倫的說法。如果武俠小說中的世界可以看做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縮影,而女性的存在依附於男性而生又幾乎是武俠世界中的必然,從精神分析的觀點來看,我們會發現,的確是有某種觀看/認同方式特別容易使女性被定位/將自己定位於這種「他不看我時我彷彿不存在」的處境,而《天龍八部》中段正淳的眾情人所展現的侵略、報復等行為與這種觀看方式更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些女子觀看自身及他者的模式顯然頗有問題,以至於段正淳「不看她」(不將之視為慾望的客體)的時候就導致其主體存在意義的虛無,甚至種種毀滅性的舉動。透過對金庸文本的分析及對精神分析相關理論的釐清,本論文將試圖證明,只有當這些依附男性而生的女性角色體會到慾望主體的真相其實是「我不看它時它就等於不在」,她們才能逆轉「他不看我時我就不存在」的宿命。 在《天龍八部》中,與段正淳有過一段情的女子在他離去之後幾乎仍過著被過去情感牽絆、沒有主體性可言的生活:或者如秦紅棉自名幽谷客,大有自戀自憐「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第七回,金
268)之意,在隱居的生活中則不時練著段正淳曾傳授她的五羅輕煙掌來回味過去;或者如王夫人在山莊種滿茶花,以此為留住遠去的情人的方式;或者如段正淳的元配刀白鳳,因丈夫處處留情而出家,成了云空未必空的玉虛散人;不過這些為情所困的女性顯然有別於傳統描繪下願意為男主角犧牲一切的癡情女子,因為她們幾乎都有著極強的攻擊慾與報復心:每練一次五羅輕煙掌就要發一次脾氣的秦紅棉以追殺段正淳其他情人為終生職志、嗜種茶花的王夫人不是憐花葬花的溫柔女子而是慣將負心漢處死做花肥的狠角;而刀白鳳則以委身「天下最醜陋、最污穢、最卑賤」的男子來報復丈夫的薄倖;至於段正淳的情人中最令人髮指、由愛生恨地將段正淳肩頭肉都咬下的馬夫人康敏,更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角色;自負美貌的她竟因為喬峰正眼也不瞧她一眼就設下毒計加害他,喬峰看不看她真的有那麼要緊嗎?何以他對康敏美色的視若無睹竟然釀成後來一連串的悲劇?我們不妨就從極度自戀的康敏開始,來看看自戀的觀看模式究竟是如何進行的、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一、一切從自戀開始 馬夫人惡狠狠的道:「你難道沒生眼珠子嗎?恁他是多出名的英雄好漢,都要從頭至腳的向我細細打量。有些德高望重的人,就算不敢向我正視,乘旁人不覺,總還是向我偷偷的瞧上幾眼。只有你,只有你……哼,百花會中一千多個男人,就只你自始至終沒瞧我[…]洛陽百花會中,男子漢以你居首,女子自然以我為第一。你竟不向我好好的瞧上幾眼,我再自負美貌,又有什麼用?那一千多人便再為我神魂顛倒,我心裡又怎能舒服?」(第廿四回,金1024) 關於自戀,最通俗的詮釋便是個體對自我的過度愛戀。至於自戀與女人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淵源久遠,不但現在普遍的社會價值觀仍然認為女性比男性來得自戀,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依德更早已指出女人與自戀有著不解之結。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解,自戀是一種由自身,而非他人,來激起性覺醒的現象,有原初自戀(primary
narcissism)和次發自戀(secondary narcissism)之分;前者指的是嬰兒期喜歡自己的身體,以自己的身體做為慾力(libido)的對象,從而獲得滿足,後者則是指兒童期以後,個體將自己原應外投的慾力收回,由愛戀別人轉而愛戀自己,從而陶醉於自我想像之中。根據佛洛依德的看法,次發自戀基本上自然是一種女性的特質,因為女性的陽具欽羨(penis-envy)會使她們感覺到先天上劣於男性,而為了補償這種匱缺感,女性就會不由自主地在後天上尋求對抗這種失落感的方式—因而高度地關懷、欣賞、愛戀自己的容貌。相對的,男性既然不受陽具欽羨之苦,也就較少呈現出自戀的傾向。做出這樣的推論之後,佛洛依德還特別強調這並非出自他個人詆毀女性的慾望(Gay
555):女性,特別是外貌好看的女性,分外會藉由自戀來尋求自我滿足,因為社會對於她們可以選擇的愛戀對象實在是強加了太多限制;她們不但因此特別有自戀的傾向,而且在感情的模式中也是需要被愛,而不是主動去愛(Gay
554)。在此,用陽具欽羨來斷言女性會因感到自身的匱缺而發展成過度自戀,實在有本質論的嫌疑,我們當然可以指控這是男性精神分析師對女性的污名化,然後一舉切斷女人與自戀間由來已久的強制聯結,但佛氏關於社會的種種箝制會把女性推向自戀一途的這項觀察,其實是頗值得重視的。當父權社會予以女性重重制約,使其做為主體的慾望與行動多受打壓而不得滿足時,女性是否有可能傾向於把自己當成一個被慾望的客體,藉由把被壓抑的愛戀與慾望投注於自己身上來得到滿足,也因此即使當她在面對愛戀對象時,也往往是延續著自戀的模式,希望被愛、被注視,而不懂如何主動去愛?以下精神分析式的閱讀也許可以提供我們一些線索。 和段正淳有過一段情、嫁給馬大元、色誘白世鏡及全冠清的馬夫人康敏,其所做所為可以說是把自戀發展到極至的具體代表,陳墨評其為「自戀成狂」—「她的一生只愛她自己。她的美貌,她的智慧,她的心願,她的花衣服,她的情郎……她的她的!一切都是她的![…]她從來也沒有愛過丈夫馬大元;也從來沒有愛過其他的人(甚至包括段正淳),並且永遠也不可能愛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情愛金庸》
211)—恐怕沒有任何讀者會有異議。不過康敏的自戀是否「已經是不可理喻,從而一般的人無法猜知她內心的究竟,她的言行舉止,也無法被人所預料、所理解」(《情愛金庸》211-2),倒也不見得那麼絕對;從精神分析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一窺這種自戀機制的運作方式。在康敏的例子裡,我們會發現一個疑點:如果自戀指涉的是像西方那希塞斯(Narcissus)愛上自己水中倒影的例子一樣,那種自信地認定自己就是最值得愛戀的對象、不假外求的狀態,那麼自戀成狂的康敏大可以不受任何外界的影響,肯定自己是最美貌的女子,至於在她口中不算什麼東西,「不過是一群臭叫化的頭兒,有甚麼神氣了?」的喬峰看不看她,又何損她對自己美貌的認定?
從這個弔詭的現象,我們正可以追索出自戀的觀看模式本身如何的脆弱:不但需要仰賴他者的凝望來支撐,更是侵略與攻擊慾的本源。 不同於佛洛依德以本質論的陽具欽羨理論來解釋自戀,法國精神分析巨擘拉岡以鏡像階段(mirror
stage)來闡釋自戀的機制如何形成及運作,顯然更具有啟發性。對拉岡而言,六到十八個月的幼兒對自己的鏡像即有特殊的迷戀:人類的出生就解剖學而言其實屬於一種特殊的早產(premature
birth),亦即在系統發育尚不完整、尚帶有母體殘留體液時便已出生。這個有所欠缺的主體卻能在鏡子中認出自己的形象並且表現出對鏡像的無窮興趣,究其因,是要藉由鏡像所提供的完形(Gestalt)來實現自己期望成熟的目的,換句話說,鏡像認同乃是一個「從不足到期待」(from
insufficiency to anticipation)的過程,主體藉此將其實並不完整的身體透過鏡像所提供的幻覺形象延伸為全形(Lacan
1977: 3-4)。這樣的原初自戀雖然是主體最早期的認同方式,因此負有不可或缺的階段性使命,但是精神分析也同時強調不能久滯於此階段,而必須接受伊底帕斯化的過程,進入象徵體系之中。鏡像認同到底有什麼樣的問題,使得精神分析理論不斷強調走出鏡像期的重要性?拉岡對此的解釋是,當主體透過鏡像認同來認識自己的時候,他其實也同時發生了異化(alienation)的現象(Lacan
1993: 39):因為他畢竟是靠著那外於自身的他者(other)才認識到自己的存在,因此「我是完整的」此鏡像幻覺成立的同時,也是「我是分裂的」這個事實被揭露的時刻;鏡像認同的弔詭便在於「我就是他者」(Lacan
1993: 39)。而正因身體形象從匱缺延伸到完整的期待過程是建立在內部衝突矛盾的鏡像認同上,這種主體內在的衝突所造成的結果便是「攻擊性的競爭」(aggressive
competitiveness)(Lacan 1977: 19),主體和他的鏡像既同一又分離的這種情境將使他成為「自己的敵對」(a
rival to himself) (Lacan 1977: 22)。說得更淺白些,就是主體要靠鏡像他者才能成立自己的這個現象,會使他憂心被他者所取代或控制,因此對他者產生攻擊的慾望。泰瑞莎•布南(Teresa Brennan)因此表示:雖然主體是透過對自己身體的執戀才建立分離主體(a
separate being)的,但這種將自己視為全能的幻想也必將帶來企圖操控(鏡像)他者的慾望(98-9)。職此之故,如果自戀的想像認同稍後不能被象徵認同所取代的話,將會使主體在對待他者時,始終與之處於在想像層次不斷角力的關係之中,既要靠他者來確立自己的存在,又唯恐他者威脅自我的生存,就此陷入嫉妒、偏執、不斷攻擊的危險中。 回到金庸小說的文本,我們可以說康敏的表現正吻合自戀模式所造成的種種苦果。乍看之下,康敏已經極度自滿其美貌,喬峰看不看她有什麼關係?經過精神分析對自戀的解讀,我們可以知道喬峰看不看康敏對她而言當然是大大的有關係;因為自戀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一個穩定及自給自足的結構,反而在根本上就是需要某種「外援」才能成立的:那希塞斯也需要水中的倒影才能自詡為最值得愛戀的慾望標的物。康敏先前能自誇為百花會中群芳之冠,是因為無數男子眼中都流露了對她姿色的傾慕,這些英雄好漢、德高望重之人因此都如同她的鏡子,印證了她是值得被慾望的、被愛的這樣的自戀信念,但是正因為自戀要建立在這種他者的凝望之下,所以康敏自恃美貌的信念絕對不是不可搖撼的;我們看到,當喬峰竟然對康敏視而不見時,康敏的自信就受到了嚴重的衝擊:當康敏指責喬峰「眼光在我臉上掠過,居然沒停留半刻,就當我跟庸脂俗粉沒絲毫分別。偽君子,不要臉的無恥之徒。」(第廿四回,金1024)時,她的言語間已經充分流露出她的不確定與不安全感,她不能肯定她是不是真的有別於庸脂俗粉之姿,而這樣的不安是她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只有靠攻擊喬峰—認定喬峰不看她的原因是出於是假正經、逞英雄、是偽君子,而不是因為她自己真的不夠吸引人。其實康敏心裡是否相信自己的說詞?答案應該相當明顯:自戀機制本身結構性的脆弱使康敏無論如何自負美貌,都還是不能自給自足,必須透過與他者的鏡映關係才能完成從不足到期待的過程,而這個期待一旦被喬峰破壞,她無法承受自身不足的結果,便是轉而用攻擊他者來說服自己「不是我不夠好,是他有問題」。 康敏在全書中的份量雖然不重,但出場時卻總是令人印象深刻,這除了是因為她策劃以陷害喬峰及段正淳的毒計招招陰險之外,也因為她連招供自己的罪行時都顯得那麼志得意滿。當她告訴段正淳自己為什麼要陷害他時,她先說了一個自己小時候如何害了「花衣服的相思病」的故事,敘述自己過年時盼不到新衣服,又眼見隔壁江家姊姊有新衣可穿,便如何偷偷到隔壁江家剪壞別人的新衣服: 我拿起桌上針線籃裡的剪刀,將那件新衣裳剪得粉碎,又把那條褲子剪成了一條條的,永遠縫補不起來。我剪爛了這套新衣新褲之後,心中說不出的歡喜,比我自己有新衣服穿還要痛快。(第廿四回,金998) 康敏這番話的目的當然是為了進一步告訴段正淳,她不只對花衣服如此,對人也是如此,如果得不到,就要毀掉: 我要叫你明白我的脾氣,從小就是這樣,要是有一件物事我日思夜想,得不到手,偏偏旁人運氣好得到了,那麼我說甚麼也得毀了這件物事。小時候使的是笨法子,年紀慢慢大起來,人也聰明了些,就使些巧妙點的法子啦。(第廿四回,金999) 這番自述不僅在字面上透露出,康敏得意洋洋於會使聰明法子,是一種嚴重自戀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再次展現了自戀所導致的侵略慾。 自戀模式中「有他就沒有我」的互斥關係是如此不穩定,以致於主體總是想著要取得主控的位置(Lacan
1993: 93),對待他者的態度也因此充滿攻擊慾,滯留在想像的層次不斷與他者進行拼個你死我活的爭鬥,這也正是精神分析中所說的「邪惡之眼」(evil
eye)的運作邏輯:「嫉妒」(“invidia”)這個拉丁字乃是以「去看」(“videre”)為字根,拉岡據此將嫉妒與觀看做一連結,表示嫉妒是充滿了貪婪慾念的邪惡之眼與生俱來的力量。而嫉妒與「渴望」、「想要」(avoir
envie)不能混為一談,因為在嫉妒中,慾望的運作並非指向主體真正需要的東西,而是當主體覺得別人的形象看來比自己完滿時,就會自覺黯然失色,更因此覺得他者威脅了自己的生存,從而產生嫉妒的情結,不管自己到底需不需要別人所擁有的那樣東西,就按照別人的慾望複製自己的慾望,對別人的慾望物產生邪惡的貪念(Lacan
1981: 115-6; Lacan 1993: 39),我們甚至可以說,邪惡之眼在沒有看到別人有那樣自己沒有的東西之前,根本不覺得自己那麼想要那樣東西,然而一旦看到別人有自己沒有,別人比自己完整這樣的感覺就會使他認定自己是真的極度渴望那樣東西。康敏的極度自戀自然也會使她的渴望化為一雙邪惡之眼,完全撇開需要的問題,任由毀滅性的慾望蔓延。陳墨在評論康敏的「新衣情結」時,曾表示康敏這個情結的關鍵在於她想要的是「新」衣服,而段正淳、馬大元、喬峰等等都只是一件一件的新衣服,她想穿就穿想脫就脫,並進一步表示「想要穿新衣服,這本是人類的一種極普遍的慾望,女性尤其如此」(《人性金庸》101)。姑且不論想穿新衣是否為女性特有的慾望,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其實是「想穿新衣」這個情結所透露出的需要(need)與慾望(desire)的差距。穿衣,是保暖禦體的基本需要問題,穿「新」衣卻不是,沒有人非需要新衣不可,所以對新衣的「需求」其實已經是進入慾望層次的問題了,至於康敏對新衣服的慾望,更不折不扣的是出自她邪惡之眼的貪慾:如果康敏是單純的想要新衣服,她再不擇手段,也應該會選擇去偷走衣服據為己有,而不是以剪爛別人的新衣服為樂。事實上,康敏稍早的言談間就已經透露了她對新衣服的渴求根本是一種與需要無關的慾念作祟:當被康敏下了藥的段正淳醉醺醺地表示如果知道當年的康敏如此渴望新衣,要他送十套二十套給她都不成問題時,康敏的回答是,「有十套、二十套那就不希罕啦。」(第廿四回,金
998),這裡當真道破了邪惡之眼的觀看模式—重點根本不在於有多少衣服,而是當東西不是你的、你得不到的時候它就特別顯得希罕!拉岡在闡釋邪惡之眼的時候,所舉的例子便是,已經不需要母親哺乳的哥哥如果看到弟弟在吸吮母乳,由於邪惡之眼的作祟,依然會嫉恨地看著弟弟(1981:
116)。康敏對得不到的新衣、對擁有眾多情人的段正淳所展現的幾近變態的渴望也是一樣的心態:她自認為為新衣服害了相思病、認為自己深愛著段正淳,但又會去把衣服毀掉、想把段正淳害死,這種愛恨綜合的矛盾正是自我與他者(鄰居姊姊、段正淳其他情人)爭鋒的鏡映關係中,嫉妒的邪惡之眼必然造成的現象。 當社會價值觀傾向於把女性與自戀連結的時候,對某些女性主義流派而言,全面挑戰父權價值體系、歌頌被父權體系污名化的女性特質一直是抗爭的途徑之一,不過就自戀這個特質而言,我們發現這種反向的歌頌恐怕不是很理想的一種方式,我們透過康敏來檢視的自戀機制足可說明自戀可能造成的災害。而康敏最後竟然因為在鏡中看到自己被阿紫毀容的醜陋模樣而氣絕,更無巧不巧地為過度自戀、沈溺虛幻脆弱的鏡像所帶來的惡果,做了一個最好註解。 二、從想像認同到戀物癖 比起馬夫人康敏,段正淳的其他情人雖然不至於自戀至此,卻多也困在想像認同(imaginary
identification)的處境中不能自拔。前面已談過鏡像期與自戀等理論,而這裡所說的想像認同其實便是指自戀與鏡映關係所在的場域,用拉岡的圖表來說明,就是圖示L(schema
L; Lacan 1993: 14)中 連接aa’(a為代表自我的ego,a’代表對應於鏡像自我的他者)的軸線。
在這個關係圖中,主體所在的位置是在S,相對於主體而言真正的他者則是代表象徵秩序與潛意識的大他者(Other),而主體的建立也是透過與大他者(Other)互動所完成的[1],但是主體最原初的建立方式就是想像的鏡像認同,也就是會把從a’(他的鏡像、相對於他的小他者)那裡所看到的,當成是主體的所在,從而建立自我(ego),這也就是圖中從S(主體)出發的線為何先指向a’(小他者),之後又沿著想像的軸線到達a(自我)(Dor
161-4),而aa’所構成的想像軸線同時也形成了一道語言牆(the
wall of language)[2],使大他者與主體被分隔在遙遙相對的兩端,主體因此也不易直接企近自己潛意識的真相,這也就是為什麼從大他者發出的線條經過語言牆的阻隔後會成為虛線;而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要讓主體理解到想像認同的虛妄,才能於象徵秩序中安身立命。所謂在象徵秩序中安身立命,是必須超越自我與小他者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瞭解到自己所面對的他者們同樣也是一個個的主體,有其獨立的慾望運作模式,因此想用一己的自我去控制管束他們必定是徒勞無功的,唯有接受這個現實,才能在面對分離(separation)—不管是原初母子共生幻象的結束,或是認清鏡像和自己的區隔,或是接受失落所愛之物之後,在象徵秩序中尋求種種的替代,展開自己做為主體的慾望辯證過程。 在《天龍八部》中,段正淳的情人們在與愛人分離之後顯然都沒有辦法在象徵秩序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她們的生命意義建立在被段正淳視為慾望客體之上,只有當段正淳這個小他者持續給予如鏡像對自己的凝望時,她們的自我才能穩固下來,一旦失去了他者的凝望,主體就或者因為自我完形的無法確立變得惶惶不安、或者要靠攻擊他者來勉力維持住自我的完整;前者如甘寶寶與阮星竹,後者如刀白鳳、秦紅棉、王夫人。段正淳情婦之一的俏藥叉甘寶寶雖然再嫁,卻憂怨度日,初見段譽時,連聽到他的大理口音、獲知他姓段都足以使她思及故人而神思恍惚,忘記身陷險境的女兒(第二回,金79-80),後來再與段正淳相遇時,雖然力圖謹守已婚婦人之份際,但卻不時可以看出她難忘舊情而哀怨不已(第九回,金
379-80);而阮星竹對段正淳的癡戀更是到了即使被他用花言巧語所哄也甘心的地步:「『我叫你永遠住在這兒,你也依我嗎?[…]你就是說了不算數,只嘴頭上甜甜的騙騙我,叫我心裡歡喜片刻,也是好的。你就連這個也不肯。』說到了這裡,眼眶便紅了。聲音也有些哽咽。」(第廿二回,金928-9)。至於段正淳的元配刀白鳳,她的攻擊性則表現在報復的慾望上;她不惜「找一個天下最醜陋、最污穢、最卑賤的男人來和他相好」(第四十八回,金
2014)以報復段正淳—得不到丈夫完整的愛,就寧可作賤自己,強迫自己委身於讓她乍見之下驚恐不已、要轉身逃開的叫化子。刀白鳳這麼做,看似給了段正淳一個最好的教訓—他一生風流,私生女無數,但到頭來很諷刺的是,他視如己出的唯一兒子段譽竟是妻子與別人私生的,而他還為了保護這個兒子不惜讓慕容復把他的眾情人全部殺掉!然而刀白鳳的一生其實何嘗有其作為一個主體的意義?她又何嘗因為遂行這樣的報復稍微減輕了自己被丈夫背叛的痛苦?更不堪的是,她自己因丈夫的出軌而傷心欲絕,所以認為用同樣的方式就可以達到報復丈夫的目的,但其實段正淳至死都不知道段譽的身世,又怎會被她的報復行動所傷害?刀白鳳所得到的報復快感,終究不過是來自於自己想像的投射:「你對不起我,我也要對你不起。你背著我去找別人,我也要去找別人。你們漢人男子不將我們擺夷女子當人[…]我一定要報復,我們擺夷女子也不將你們漢人男子當人」(第四十八回,金2013),結果我們看到,這自暴自棄的一次出軌,並不能使刀白鳳就此脫離為段正淳所負的陰影,只是徒然在自我與他者的角力中亦步亦趨地受制於他者的所作所為,在攻擊他者的時候也傷害了依附他者而生的自己。接著看秦紅棉。秦紅棉的生命似乎以追殺段正淳的其他情人為目的,行徑雖不似康敏般變態,卻也是攻擊慾極強的例子,她不但把自己的生命浪擲在追殺情敵上,也灌輸女兒木婉清天下男子皆薄倖的觀念,要她立下毒誓,若有人見了她的臉,假如不殺他就得要他娶她,而丈夫若是負心又必須親手殺了他,一旦有違誓言、下不了手的話,就得自刎(第四回,金161),這樣一種在女兒身上複製自己偏執的思考的行徑,表面看起來是保護女兒以免她受一樣的苦,其實也暴露出秦紅棉對自己被拋棄一事不曾忘卻,更無法擺脫被拋棄之痛苦,女兒若是真的遇上負心漢而將他殺了,倒也是可以為她帶來替代性的滿足—自己不能(不忍)手仞段正淳,但卻希望天下負心漢能夠死盡!另一個希望天下負心漢都死盡而且更為變態的角色自然就是王夫人阿蘿。事實上,王夫人的侵略慾及變態行徑可說不遜於馬夫人,而她所表現出來的一項其他女子沒有的變態傾向則是戀物僻(fetishism),以下我們就來看看這種心理機制和想像認同之間的鉤連。 關於戀物癖,佛洛依德所提出的解釋依然是充滿陽物理體中心(phallogocentrism)的色彩,對他而言,戀物癖中受到崇拜愛戀的物神(fetish)基本上是陽具的替代品:
正常的情況下這陽具應該被放棄,而物神就是特地設計用來防範陽具消失的東西。說得更淺白些,物神是母親的陽具的替代品—小孩子一度相信母親[和他一樣]有陽具,但基於種種我們並不陌生的原因,他可能不願放棄這陽具。之後所發生的現象,就是小男孩拒絕承認他發現女性沒有陽具的這個事實。不,這不可能:因為如果女性是因為被去勢才沒有陽具的話,那麼他自己擁有的陽具豈不也處境危險?為了反叛這樣的情況,他對陽具這個特別的器官本能的防護,使他的自戀情結油然而生。(SE
XXI 152-3) 也就是說,佛洛依德認為戀物癖是小男孩為了否認(disavow)去勢恐懼所發展出來的傾向。正常的情況下,接受了去勢恐懼的小男孩會進入伊底帕斯化的過程,知道不能依附在母子共生的想像階段,也就是說戀母有可能會使他的強大對手—父親—將其去勢,所以小男孩會發展出對父親的認同,以期自己長大後能夠擁有母親以外的其他女性作為其慾望客體;而戀物癖者則是從這樣的常軌中逃逸,他們對自己的陽具所投注的自戀使其不能處理瞥見女性生殖器所造成的去勢恐懼,因此選擇相信女性也是有陽具的,為了要否認這個他們明明已經看見的事實,戀物癖者所採取的折衷之道—當然不是在意識層次選擇這麼做,而是根據潛意識法則的引導—便是堅持相信女性有一個不同於他原先所認定的陽具,也因此替代陽具功能的物神就出現了,透過這個物神,他把原先應投注於生殖器官的性滿足轉從物神身上得到。佛洛依德認為男性戀物癖的對象物常常是女性的內褲,原因在於那是女性把衣物卸盡、露出沒有陽具的真相的前一刻,在這一刻,他還是可以相信女性是有陽具的(phallic),所以他選擇了這個關鍵物為物神(SE
XXI 155)。
關於戀物癖這個問題,法國女性精神分析師克莉斯提娃(Julia
Kristeva)也做了一番值得參考的補充。根據克莉斯提娃的論點,戀物癖的確和鏡像期的自戀情結有關。小孩對鏡像投注驅力(drives)的原初自戀期,奠定了後來他可以區分人我、自身與外物的的基礎:小孩最早安置/確立(posit)的物件(object)便是鏡像中的自我,而認識到鏡像畢竟外於自身之後,他將能接受與母親分離的經驗,在象徵秩序中一一安置/確立其他物件/客體的存在,也就是展開他象徵表意(signify)的過程,利用語言的表意來昇華原初的失落感(Kristeva
1984: 46);但是鏡像期的經驗如果不能被適當的轉化發展,那麼就有可能變為窺視狂(scopophilia),始終需要一面鏡子或替代鏡子功能的受話者(addressee);或者是變成戀物癖者,抗拒承認他發現母親被去勢的這件事,運用戀物癖的機制使陽物母親的存在可以確立。克莉斯提娃認為其實戀物癖也許不是在發現母親被去勢的時候才出現的,更早期對自己鏡像的依戀、不能將鏡像與實際身體分離開來的問題也將造成戀物癖的形成(1984:
63)。總之,不論是因為不能與母親分離所以認定其為陽物母親(phallic
mother),或是深陷於鏡像誤識之中所造成的戀物癖,都是一種透過戀物回返自體快感(autoeroticism)的機制(1984:
65),是正常的表意功能停滯的一種表現,因為表意功能是要主體學習用語言去指涉,同時瞭解使用語言就是接受失落(必然是當下缺席(absent)的東西才需要靠語言來再現(represent))的這個事實,而戀物癖者卻不使用語言,而使用物件(objects)來表意(1984:
64)。
在以上的理論中,佛洛依德的看法因為傾向生物決定論,因此令人不解的是如果從對陽具有無的在意來解釋戀物癖的產生,那麼本來就沒有陽具、也就沒有去勢恐懼的女性是否就不會有戀物癖的出現?克莉斯提娃的補充則把戀物癖連結到鏡像期所發生的問題(disorders
in the mirror stage)之上,因而可以解釋兩性都有可能出現戀物癖。其實,如果我們按照拉岡對佛洛依德去勢效應的修正來看這個問題,會更為清楚;拉岡認為去勢效應並不必定指小孩對失去陽具的恐懼,而是小孩與母親分離的經驗中,發現自己不是母親唯一愛著的對象(因為還有父親),母親有著他所不瞭解的、不可知的慾望,因此深感自己一定失去了什麼東西(Lacan
1957-1958, seminar of January 15, 1958, qtd. In Dor 115)這樣的一種原初失落,換句話說,戀物癖不必然只發生在不承認母親在生理上被去勢的男孩身上,也發生在明知已然失落了愛物卻不願意接受失落或分離經驗的任何主體身上。王夫人對蔓陀山莊的茶花所投注的特殊情感,正是一種戀物癖者與物神的關係,用以否認情郎段正淳已經不在身邊的事實。
用來讓自己對失落視而不見的物神具備了什麼樣的特質呢?這裡我們可以參考馬克斯在分析商品物神化的現象時所提供的看法:「在金幣作為交易媒介的階段,貨幣本身依舊帶有使用價值的色彩。但因在頻繁的交易流通過程中金幣本身的物質性會不斷耗損,變得越來越名不符實—金幣本身所代表的價值不符現有的實質—遂導致金幣後來逐漸為銅幣、鎳幣、甚至紙幣所取代。也就是說,整個貨幣的流變是往愈來愈名不符實的方向走(Marx
11-4),變得越來越鬼魅。正如齊傑克(Slavoj Zizek)所言,錢幣擁有一種難以言喻、崇高(sublime)的『非物質肉身性』(immaterial
corporeality)—縱使肉身不斷消磨耗損,但它所象徵的價值依舊恆常不變(18)」(Chiou
106)。簡單的說,物神必須超越該事物本身原本的價值、對主體產生無法名狀的特殊魅力,也就是必須產生溢乎其「物質肉身」的吸引力。那麼什麼樣的東西特別可能成為物神?它通常必須和主體不願與之分離的對象有所關連。段譽曾經猜測到王夫人分外喜愛茶花的原因「定是當年爹爹與她定情之時,與茶花有什麼關連」(第四十七回,金1985),這個推測後來在王夫人死前從段正淳與她的對話中得到證實:「我對你的心意,永如當年送你一朵蔓陀花之日。」(第四十八回,金2032);王夫人當年與段正淳在姑蘇的蔓陀山莊定情,段正淳離去後山莊依然種滿大理的山茶花,而且就連後來她用計要擒拿段正淳時,所購置的莊子也是種滿了茶花,茶花的布置還和當初一模一樣,這些都足以證明王夫人對茶花的喜愛不只是喜歡茶花本身,其實更是在延續對段正淳的情愛,否則她也不會連品種都不懂卻還是癡戀著段譽眼中一盆盆的俗品茶花—把大理人嘲諷命名為「落第秀才」的雜色茶花視為至寶、把白茶「紅妝素裹」、「抓破美人臉」都當成「滿月」……等等,王夫人的「焚琴煮鶴」、「不懂山茶,偏要種山茶」(第十二回,金493)在段譽看來十分無稽,但其實只要瞭解茶花對王夫人的象徵意義,就可以理解何以她愛茶花卻不識茶花本身「物質肉身」的價值。王夫人或許本來就已極愛茶花,但是茶花被提升到物神的地位,卻定是段正淳的離去所造成的,藉著大理盛產的茶花,住在蔓陀山莊的她與住在滿是茶花的鎮南王府的段正淳之間,也彷彿還有著聯繫。
段譽曾經揣測,王夫人「一捉到大理人或是姓段之人便要將之活埋,當然是為了爹爹姓段,是大理人,將她遺棄,她懷恨在心遷怒於其他大理人和姓段之人。她逼迫在外結識私情的男子殺妻另娶,是流露了她心中隱伏的願望,盼望爹爹殺了正室,娶她為妻」(第四十七回,金1985),其實除此之外,王夫人動輒把大理段氏的人、在外另有情婦又不肯殺妻另娶的人捉來活埋做茶花花肥的這種行徑,也可以看出王夫人絕不只是單純地喜愛茶花:透過茶花來思念、埋怨、痛恨段正淳,無非都是處心積慮地用茶花來維繫住與段正淳的一絲關係。王夫人原本也要將闖入山莊的段譽折磨至死再做成花肥,卻因他說起茶花頭頭是道便願意設宴款待他,在席間段譽侃侃而談茶花的正品副品如何區分、有哪些名種,王夫人聆聽得悠然神往之際,自言自語了一句「怎麼他從來不跟我說。」(第十二回,金496),這裡實在是點破了茶花在王夫人心中如此重要的關鍵所在:分離已成事實卻不能接受,戀物癖者只有憑藉著物神,停滯在分離之前的完滿幻象中,而無法在象徵秩序中開展自己慾望的辯證。而連王夫人想計擒段正淳時,也是利用過去段正淳吟過的詩詞「春溝水動茶花白/夏谷雲生荔枝紅」、「青裙玉面如相識,九月茶花滿路開」(第四十七回,金1979-80)做成填字遊戲,企圖引段正淳入甕,她牢記當年與茶花/段正淳有關的種種,始終停留在過去回憶的心態,不言自明。
不論是自戀或是戀物,困在想像認同的層次中等待他者的凝望來成立自我的結果,便是主體的極度異化、有抒解不完的攻擊慾。段譽感嘆父親的舊情人,包括自己母親,個個脾氣古怪(第四十七回,金1996),實非無的放矢。最後這些女人(除了康敏之外)全部同歸於盡的場景中,特別加以刻畫、也因此分外值得玩味的,便是王夫人的死:當慕容復殺了阮星竹、秦紅棉、甘寶寶卻仍不能使段正淳屈服時,王夫人雖然是慕容復的舊母,卻也開始心驚有性命之虞,此時段正淳對她柔聲道:「阿蘿,你跟我相好一場,畢竟還是不明白我的心思。天下這許多女人之中,我便只愛你一個[…]你外甥殺了我三個相好,那有什麼打緊,只須他不來傷你,我便放心了。」段正淳這番話使王夫人害怕莫名,因為她知道段正淳恨她至極,才會故意說反話讓慕容復把她也殺了,但是之後的變化則更為戲劇性: 王夫人素知道外甥心狠手辣[…]只要段正淳繼續故意顯得對自己十分愛惜,那麼慕容復定然會以自己的性命相脅,不禁顫聲道:「段郎,段郎!難道你真的恨我入骨,想害死我嗎?」 段正淳見到她目中懼色、臉上戚容,想到昔年和她的一番恩情,登時心腸軟了,破口罵道:「你這賊虔婆,豬油蒙了心,卻去喝那陳年舊醋,害得我三個心愛的女人都死於非命,我手足若得了自由,非將你千刀萬剮不可…...」他知道罵得越厲害,慕容復越是不會殺他舅母。 王夫人心中明白,段正淳先前假意對自己傾心相愛,是要引慕容復來殺了自己,為阮星竹、秦紅棉、甘寶寶三人報仇,現下改口斥罵,已是原諒了自己。可是她十餘年來對段正淳朝思暮想,突然與情郎重會,心神早已大亂,眼見三個女子屍橫就地,一柄血淋淋的長劍對著自己胸口突然間腦中一片茫然。但聽得段正淳破口斥罵……比之往日的山盟海誓,輕憐密愛,實是宵壤之別,忍不住珠淚滾滾而下……(第四十八回,金2031) 最後王夫人更在段正淳斥罵不休的情況下,猛然自己撞向慕容復的劍尖結束生命,不但段正淳要吃驚何以王夫人不解他的斥罵是要救她一命,讀者可能也極驚訝於王夫人竟神智不清、顛三倒四至此,先前還知道段正淳若假意示好才是恨她的表現,瞬時間竟然又認為段正淳如此嚴厲的話語是恨她的表現。這一段的曲折寫得極細緻,我們就此可以再次看到想像認同造成的問題。先前說過,當主體困在oo’的想像軸線上時,這軸線會形成一道語言牆,阻隔了真正對話的進行—每一個主體的語言行動其實都受到了慾望的穿透,必須放在代表大他者的象徵體系中才能理解,不能只從自我的位置出發,以想像投射的方式理解字面上的意思。王夫人起初意識到這一點,知道段正淳語言中的慾望是要置她於死地,但是當段正淳心軟改口罵她時,她卻因為心神已亂,分不清楚段正淳口頭上的辱罵是否正是他的真心,因此把自己棄婦哀怨自傷的心情--「你從前對我說過甚麼話,莫非都忘記了?你怎麼半點也不將我放在心上了?」(金2031),一股腦投射到段正淳身上;說話者的發言位置、發言慾望這些東西都被摒除在想像軸線之外了,此刻段正淳所說的話聽在王夫人的耳朵裡之所以只具有字面上的辱罵仇恨之意,實在是因為王夫人幾近偏執的狀態,使她所聽見的成為一種「錯覺的言說」(delusional
speech),自己心裡懷疑、焦慮、認為對方會如此看待自己的種種信息,會反向地透過錯覺中的小他者之口被主體接收(receiving
somewhere her own message in an inverted form from the small other;
Lacan 1993: 52-3)。而偏執的想像認同所造成的結果,自然是使王夫人認定段正淳不但離棄她還恨她,因而決定自戕,王夫人想聽的,畢竟是段正淳「輕憐密愛」之語,和阮星竹一樣,即使是口頭說說騙她,她也高興—王夫人就在段正淳許下不可能實現的承諾:明天就去大理無量山中的玉洞雙宿雙飛,之後,滿臉喜色的死去。 三、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陳墨在評析金庸小說中失戀的女子為「憂傷的情魔」時,提到了一個他認為「怪。但這就是女性」(《情愛金庸》50)的現象,這個現象,就是失戀的女人「不去恨應該恨的人(拋棄她的男人,薄情的男人或不愛她的男人),而卻偏偏要去恨那不該恨的人(她的情敵、她的同類,那個得到或『奪了』她的情郎的女人)」(《情愛金庸》57)。陳墨舉出了不少例證,如《碧血劍》中的何紅藥不恨金蛇郎君夏雪宜、不恨自己盲目,卻恨透了夏雪宜所愛的溫儀;《神鵰俠侶》中的李莫愁「也像何紅藥、王夫人、秦紅棉、甘寶寶、阮星竹……等等所有的女性一樣並不恨男人,不真的恨那『薄情郎』,而是恨自己的同類,恨另一個女子將自己的情郎奪去。以為別的女人是『小賤人』、『狐媚子』、『騷狐狸』云。」(《情愛金庸》54)。這種女人為難女人的現象在《天龍八部》中的確是甚為明顯,我們在第八回就已經看到秦紅棉與刀白鳳正面交手,雖然眼見段正淳出手相救自己的情敵時,兩人分別不滿地向段正淳進攻,但是當她們見到對方向段正淳攻擊時,又都同時要迴護郎君,即使她們之後發現段正淳是假裝受傷,思及「這傢伙最會騙人」,兩人又聯手向他進攻,但是對段正淳出手時,卻絕非像攻擊情敵時那樣,招招意圖置對方於死地。在第廿三回中秦紅棉原先意圖行刺阮星竹,在阮星竹的軟語感動下,表面上化敵為友,共同把馬夫人康敏視為使段正淳負心的罪魁禍首:「秦紅棉恨恨的道:『我和段郎本來好端端地過快活日子,都是這賤婢使狐狸精勾當……』阮星竹沈吟道:『那康……康敏這賤人,嗯,可不知在那裡。妹子找到了她,妳幫我在她身上多刺幾刀』。」(金
986);稍後我們將發現兩女的同仇敵愾並不真摯,彼此都只是假作對對方毫無戒心之狀,事實上阮星竹對秦紅棉隱瞞了段正淳的行蹤,而秦紅棉也知道她在使詐,兩女之間短暫的姊妹相稱畢竟是爾虞我詐而非相濡以沫。第四十七回,王夫人聽說段正淳又和別的女子同行,勃然大怒地質問:「……他丟下了我,回大理去做他的王爺,我並不怪他,家中有妻子,我也不怪他,誰叫我識得他之時,他已是有婦之夫呢?可是他……可是他……你說他又和別的女人在一起,那是誰?那是誰?[…]哼,這賤女人模樣兒生得怎樣?這狐媚子,不知用甚麼手段將他迷上了。」(金1996-7)。這些女人之間的恨意可說是非常分明,然而她們對共同的負心漢的心情恐怕卻一致多類似王夫人:「對他即使有所怨懟,也多半是情多於仇」(第四十八回,金2006)。
對於武俠小說中充斥的這種女人為難女人的例子,難道我們只能感嘆這就是非理性的女人特別會製造的怪現象嗎?或許也不盡然。《天龍八部》中段正淳眾情人們一致表現出來的對情敵的恨、對情人的寬容,與其用性別決定論推斷是因為失戀的女性必然會如此,不如說還是她們觀看/認同模式的結構性問題使然。前面已經說過,段正淳的情人們多停留在想像認同的層次,而因為想像認同中的自我完形只是從不足跨越到期待所產生的幻像,這種不穩定會使自我必須不斷與小他者進行爭鬥來保障自己無所匱缺的錯覺,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女子恨其他的女子而不恨段正淳的原因,或許就不是那麼怪異難解了:如果她們痛恨段正淳、真的把他看成厚顏無恥、到處留情、花言巧語的負心漢,那麼她們豈不也等於承認愛著段正淳的自己是盲目的、愚蠢的、和無恥之徒廝混的同一等人?而自己到現在心裡仍眷戀段正淳這個惡人,豈不是更為不堪?可是如果她們恨的是情敵,情況就不同了,把情敵貶為賤女人、狐狸精,她們不但保全了「情郎只是一時被狐媚所惑才誤入歧途」、「他不是不愛我」這樣的幻覺,也可以免於面對心底的焦慮:是不是我有甚麼不夠好所以他才又去愛別人?換句話說,想像認同「有他就沒有我」的結構性缺陷,將為主體製造出「打壓他就可以確保我」的錯覺,這恐怕才是這些女性彼此憎恨殘殺的深層原因。也就是說,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女性之間互相打壓貶抑是女性本質使然,而是任何過度耽溺想像認同的人都容易發生的現象。
不過我們還是得問,那麼女性是不是就是這種比較容易耽溺想像認同的人呢?法國女性主義者依莉佳萊(Luce
Irigaray)很不滿意的,就是精神分析的理論所導出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依莉佳萊認為,佛洛依德用伊底帕斯化的過程來解釋主體的形成,表示小男孩的戀母情結將會在父親帶來的去勢恐懼下受到阻止,因而發展出較強的超我(super
ego),知道要控制不應有的慾望,進入主體化的正常過程,但女孩因為本來就已經被去勢,不會受到去勢恐懼的威脅,所以戀父的情況不論持續多久都無所謂,甚至女性對父親或男性長輩那種孩童式的依賴(infantile
dependency)也是一直被允許的,因此女性的超我就變得較弱;這整套理論似乎表示女性的象徵認同較差是一種宿命、女性不像男性那樣具有社會及文化中較被肯定的種種正面價值(39-40)。佛洛依德用陽具的有無來推斷象徵認同的發展順利與否當然是大有可議之處的,但是他關於女性的戀父、依賴情結多被允許的這項觀察卻是相當重要的。事實上我們知道,不要說是武俠小說所描繪的中國古代社會了,即使到如今,社會的價值還是普遍地允許、甚至鼓勵女性的依賴情結,當女性一直被「潛移默化」為應該被保護疼愛、被男性慾望的客體時,想要超越想像認同的幻象、進入象徵秩序成為主動愛慾的主體也就變得格外困難。因此問題不在於歸咎女性生理條件會使其超我較弱、道德價值觀較低、喜歡與女性同類鬥爭,而在於檢討整個社會環境所能提供的條件是否根本在很多方面是不利於女性主體發展的。 除了佛洛依德之外,克莉斯提娃關於主體形成的理論也指出了女性主體發展的不利情況。克莉斯提娃認為,孩童若要瞭解到母親並不是和他共生的一部份、接受與母親分離的事實,很重要的一個步驟是完成象徵性的弒母(matricide),唯有透過這一個步驟,自主自發的主體(autonomous
subject)才能成立(1989: 27),反之,主體如果把母子共生狀態的結束看成是失去了自己的一部份,就會被這種自戀傷痕(narcissistic
wound)帶入憂鬱情結之中,無法進入象徵層次的主體發展。有鑑於此,主體必須進行象徵性的弒母,至於母親已死的原初失落,則要用昇華(sublimation)的方式來處理。然而昇華的方式是什麼呢?克莉斯提娃表示,對異性戀男性或同性戀女性而言,就是將死去的母親(當然是比喻的說法)當成愛慾的客體(erotic
object),透過愛戀其他女性來重新收復母親這個失落物,另外,以藝術創作的方式來達到昇華的目的更是克莉斯提娃甚為讚許的一種方式(1989:
28)。但是根據克莉斯提娃的看法,女性想完成象徵性弒母是困難重重的,「因為我就是她[母親],她就是我」(1989:
18):女兒與母親在性別上的直接認同使得她不容易透過弒母來成立她的主體。女兒的主體性,在弒母障礙的為難之下,難以發展。 在這裡特別要說明的是,雖然許多女性主體性的發展顯得較男性遲滯,的確和無法脫離依賴母親的狀況極為相關,但這種女兒與母親在性別上的直接認同並不只是生理上的必然性所能解釋的,它同時被社會文化的意識型態所穿透:例如家庭及社會環境對女孩成為「賢妻良母」的要求,便是女兒被強制(但不見得在意識層次感受到這種強制性)與母親做認同的原因之一。因此,即使精神分析的理論導引我們注意到女性在象徵認同上的困難、解釋了自戀的情況多發生在女性身上的原因,我們更必須強調的是,這並不是一種本質論的劃分,女性所受到的社會限制、昇華的管道較為侷限等因素絕對與許多女性為何難逃想像認同的牽絆有很大的關係。女人如果為難女人,並不是像部分評家所認為的那樣,是女人的天性,而是在內化了男性中心的價值觀之後,女性習慣靠著男性的凝視來決定自己的價值。試問是不是因為「女為悅己者容」這樣的價值觀深植在女性心中,所以《俠客行》中的梅芳姑才會在發現不被石清所愛之後,把原本自詡姣好的容貌毀掉?而馬夫人得不到喬峰的凝望就覺得自己再怎麼自負美貌也沒有用,是否使我們警覺到,一個無時不忘攬鏡自照的自戀女人根本不見得是真正自我肯定的女性主體?也許她根本是透過男性的眼睛來看自己、惶惶不安於是否符合美的標準、是否能成為慾望的客體而已?當我們重新檢討自戀的結構之後,會發現不論是把自戀歸為女性本質的父權意識型態,或是想把自戀歌頌為女性自信自愛的主動表現的部分女性主義流派,都有其無法觀照到的盲點。 結
語 一開始,我們便看到,存在於肉眼與凝視的辯證中的,不是巧合,而是,相反的,誘餌。每逢,在愛戀中,我索求一個凝望,令人深深不滿的,總是佚失的,便是—你絕不能從我看你的那個位置來看我,反過來說,我所看到的絕非我想看的。(Lacan
1981: 102-3)
如果陷溺想像認同的女性所犯的錯誤,在於認定「他不看我時我就等於不存在」、把生命的價值建立在被慾望(to
be desired)之上,那麼什麼樣的認知可以有助於跳脫想像認同的侷限呢?前言中提到了量子力學式的反省,就是一個很好的起點。當齊傑克把量子力學的思考引進精神分析的框架時,所舉的例子正是引起Einstein與Bohr爭議的「光的波粒二象性」的實驗:Einstein設計了一個電子通過雙狹縫干涉的實驗—當雙狹縫開啟時,從屏幕出現的亮點可以知道電子垂直方向的動量,分別關上其中一個狹縫,
就可以知道電子的確實位置;但是Bohr發現,如果關上其中任何一個狹縫,實驗的狀態就完全改變了。當雙狹縫開啟時,不管是真的有兩個電子分別通過狹縫,或者電子其實是一個個發射出來的,最後都會在屏上形成波的干涉條紋;假如輪流開啟一個狹縫,
去觀察電子究竟經過那個狹縫,最後幕屏上卻不會再有干涉條紋了;「這好像是說單一的電子(必須通過兩個狹縫之一的粒子)『知道』另一個狹縫到底有沒有打開,因此有不同的因應方式:如果另一個狹縫是開著的,它就呈顯波的型態,如果關著,它就呈顯正常粒子的型態。甚至於一個電子好像也知道自己是否正被觀測著……這個實驗要暗示的是什麼?」(Zizek
221)。這個本來是 Einstein
用來反駁量子力學的理想實驗,經由Bohr
的解釋在今日已成了說明測不準關係和互補原理的標準範例;我們在此當然不是要探討這門深奧的學問,而是要隨著齊傑克一起問,這個物理學的爭議所暗示出的哲學性思考是什麼? Einstein堅信,有一個離開知覺主體而獨立存在的客觀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學的基礎,因此一直想駁倒Bohr的觀點。為
Einstein 立傳的作家A.Pais 回憶道:「有一次和 Einstein
同行,他突然停下來,轉身問我是否真的相信,
月亮只有在我去看它的時候才存在?」[3]
。如果我們回答,「月亮只有在我看它的時候才存在」似乎顯得無稽荒謬,但是在精神分析的觀點裡這個答案卻不是沒有意義的。齊傑克便用光的波粒二象性的實驗來引申精神分析的相關概念:「我們(主體)對事物的認知會影響並且改變該事物本身:我們不能認定每樣事物均包含了自身的本質,以為不論我們怎麼看它,它『就是在那裡』……一件事物之所以完全變成『它自己』,同時會受外在的環境如何『注意到它』(take
note of it)所影響。這種事物和外在的構成關係,不就像『象徵實踐』(symbolic
realization)的邏輯一樣?某一件事物要算數、要變得有效,都是透過外於自身的象徵秩序將之加以定位後的結果」(222-3)。[4]就像在以上的實驗中,如果粒子和波的性質不曾被一套特定的象徵鑄模(symbolic
matrix)定義為互斥的、矛盾的(Zizek 225),那麼實驗的結果是否還是那麼令人困擾不解呢?在這裡齊傑克所點出的其實是精神分析非常強調的觀念,也就是對象徵定位的理解:我們在象徵秩序中的定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本質,而是透過主體、他者與大他者之間的繁複互動(如前述的L圖示)才決定的。有了這樣的認知,主體才不至於被釘死在一個固定位置上,落入宿命的本質論中,而能夠展現主體的能動力,瞭解自我與他者的關係是如何被語言、慾望、文化建構等不同因素所穿透。 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在想像認同中以為可以「獲得」他者的凝望來肯定自己是多麼虛妄的想法。飛蛾的翅膀上的假眼原本當然是為了嚇阻捕食者,但是我們不妨想想,在不把飛蛾當成獵物的狩獵者眼中,那眼狀斑點是不是形同瞎的呢?因為其實只有在打算獵食飛蛾的他者眼中,飛蛾的眼狀斑點才變得看得見東西(Bozovic
171-2)。簡單的說,這個例子要強調的便是,他者的凝望這種東西,其實是我從他者的位置想像出來的(imagined
by me in the field of the Other; Lacan 1981: 184),就像飛蛾的假眼如何會產生瞪視的效果呢?只有當捕食者把自己的慾望讀入牠的位置時,本來只是個斑點的東西才成為假眼;任何的凝望也都像假眼發出的效果一樣,凝望並不是來自飛蛾翅膀上斑點的「本質」,也因此無從被「獲得」。只有瞭解到這一點時,主體才有機會脫離渴望他者看自己一眼的窘境,轉而肯定自己作為一個慾望主體的身份:如果我總是想成為被慾望的客體,就必須因應他者的眼光,變成他想要看的樣子—其實我永遠不可能真正知道他是怎麼看我的,因此結果我只能徒然困在「他不看我時我等於不在」的處境中,但是當我肯定「我不看它時它可能形同不在」時,我卻可以變成一個有行動力的主體。當然這個層次的認知不是要我們反向地變成獨我論的自大狂,認為自己的看法對他者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是指去瞭解自己對外在事物的觀望方式、自己的慾望投射等等,在在影響到我所看到的結果、我所誤以為一成不變的客觀現實,如此才能一方面肯定自己的主體性,一方面理解象徵秩序的可改造性。 在《賞析金庸》中陳墨評道; 《天龍八部》這部小說,是一部有關人心、人性、人生與人世的深刻的寓言—其「大悲大憫、破孽化癡」的意義正在這裡。[…],可以說,這部《天龍八部》浸透了佛家的哲學思想與美學思想。它的內容來自人性—或對人性的認識—中的貪、嗔、癡的種種病態的深刻的揭示;它的意義來自對這種貪、嗔、癡的「人性之毒」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生之苦」與「人世之災」的揭發與破解;它的境界來自於對這種人生、人世、人心與人性的大悲憫與大超越。(269-70) 而精神分析的理論雖極其艱深繁複,但秉持的理念其實卻與此相當近似,便是對潛意識—舉凡慾望、毀滅、恐懼、空無、不可能的面向—的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its unconscious)(Kristeva 1991: 191)。例如雖然知道人與人之間的凝望無可避免地參雜有想像的投射與慾望的穿透等成分,我們還是應該盡可能透過自我與他者在象徵秩序中的辯證關係,去勘破其中想像的虛幻,以免被一己的執念所困,陷入想像、自戀、攻擊的惡性循環中。段正淳身邊的女性自然無一可以超越這樣的困境,而其實不能超越想像認同的又何止武俠小說中的女子而已?不論性別身份如何,如果缺乏對人自身黑暗面的認知,都很容易墮入這樣的迷障中。藉由跳出性別本質論來解讀這些女子悲劇的形成原因,本論文冀望就此開啟女性主義閱讀與金庸小說之間的溝通空間,在拒絕父權意識型態對女性的樣板化之際,能同時品評閱讀金庸小說的無窮樂趣。 *本論文的完成,要特別感謝妹妹宗潔代為蒐集相關資料以及她的辛苦校閱。 引用書目 Bozovic, Miran. “The Man Behind His Own Retina.” 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acan (But Were Afraid to Ask
Hitchcock).
Ed. Slavoj Zizek. Brennan, Teresa.
History After Lacan. Chiou, Yen-bin. “Reading Specters: On Derrida’s Desire to Be an Inheritor and
His Intervening 1995): 102-115. Dor,Joël.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ed Like a Language.
Trans. Susan Gurewich. Northvale: Jason Aronson Inc., 1997. Freud, Sigmund.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and Other Works.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XXI.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Gay, Peter, ed. The Freud Reader.
Irigaray, Luce.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Trans. Catherine Porter and Carolyn
Bruke. Kristeva, Juli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ans. Leon ---.
Black Sun: Depression and
Melancholia. Trans. Leon ---.
Strangers to Ourselves.
Trans. Leon UP, 1991. Lacan, Jacques.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Norton, 1977. ---.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1973).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Alan Sheridan. ---. The Psychoses: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I (1955-1956).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Russell Grigg. 1993. Zizek, Slavoj.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An Essay on Schelling and Related Matters. 金庸。《天龍八部》。台北:遠流,1997。 陳墨。《情愛金庸》。台北雲龍,1997。 ---。《人性金庸》。台北雲龍,1997。 ---。《賞析金庸》。台北雲龍,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