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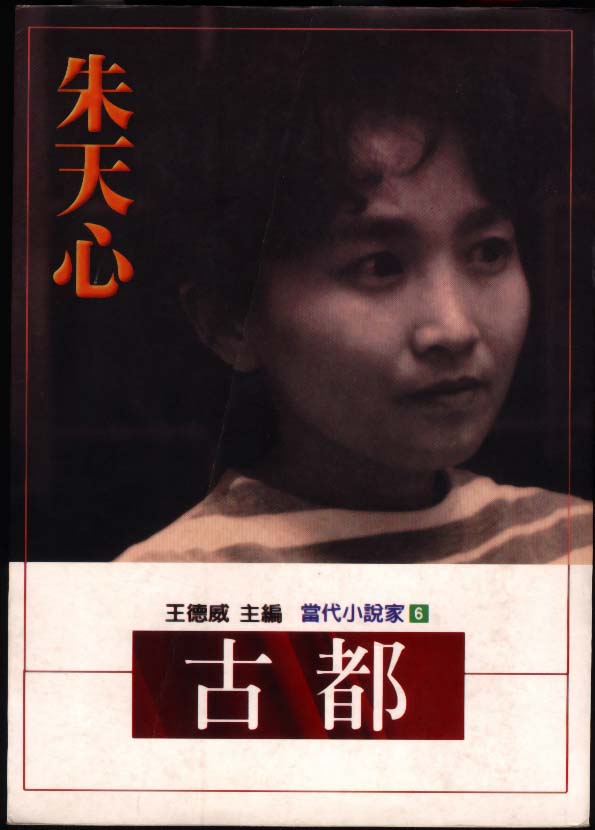
中國時報《開卷》1997.6.12
「同樣一個城市,在老靈魂們看來,往往呈現完全不同的一幅圖像。」
在〈預知死亡紀事〉中,朱天心早已如此宣告。但,或許「老」得還
不夠徹底吧?那時的老靈魂們,縱使擅於游走多方,預言休咎,畢竟還只
能以「特定」的族類身分,在「一」個「現世」的城市裡憂生憂死,且啼
且笑。而今,他/她們數歷劫毀,薈聚於《古都》,終要展現穿越多重時
空、轉換多樣身分的變貌。於是,無論是京都是臺北是桃花源,是晉太元
中是咸豐七年抑是西元一九九六,老靈魂尋尋覓覓,一路行來,追索原鄉
記憶的初衷不變,卻終因在不同時空座標的罅隙間流離失所,進退維谷,
透顯出前此未有的歷史滄桑。經由精心安排的多重文本互涉,《古都》召喚、開發著讀者們所有該
記得的與不該記得的記憶片斷。它所收的四個短篇和一個中篇,各篇著眼
點互異,卻都多少迴映了先前老靈魂的情事(如〈威尼斯之死〉之於〈我
的朋友阿里薩〉;〈拉曼查志士〉之於〈預知死亡紀事〉;〈匈牙利之水
〉之於〈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從篇題到內容雜用中外典故,驅動讀者
聯網串接至一切存在或不存在的人文想像;各篇多安排一與敘事者往還互
動的人物「A」,復使不同族類、性別、年齡的芸芸眾生,隱涵了「如此
不同,卻又如此相同」的內在聯繫,且延伸出彼此身分交換流動的無限可
能性。而這些,又以「百川赴海」的態勢,匯流至〈古都〉,並達於高
潮。中篇小說〈古都〉,堪稱是朱天心創作迄今的集大成之作。它內蘊的
深廣繁複,不僅在於綜括了自她少作以來的各重要文學場景、關懷重點,
也因有意識地將〈臺灣通史序〉、〈桃花源記〉、川端康成同名小說《古
都》等文的許多段落,以及京都、臺北的生活片斷切割錯雜,拼貼在一起
,為原鄉記憶的追尋之旅,經營出「時無分古今,地無分中外」的永恆性
與普遍性。文中主角,遂既是生活於大臺北的現代都會女子,也是緣溪而
行的武陵人、是亟欲姐妹相會的苖子和千重子。她(們)鎮日栖栖惶惶,
流離於交錯疊映的各種時空座標間隙,總要在急管繁弦時憂心曲終人散,
在斷井頹垣處追懷侘紫嫣紅。淡水河口於是可以恍若長江,大臺北竟反似
蠻荒異域。她(們)恆常是時間中的逐客,空間裡的遷人,終極原因,只
為了不甘,更不堪於曾經存在之事物的流逝改變--「難道,你的記憶都不
算數?」老靈魂幽幽問道。是的,記憶。只不過,老靈魂一不記家國興亡,二不記仕隱進退。儘
管結局同樣是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同樣是日暮途窮,慟哭忘返,卻絕不
同於屈原、阮籍等男流之輩,只知道以諫君憂民為己任。她們念茲在茲的
,毋寧是熟悉的歌聲、親切的氣味、曾眼見它蕃息滋榮,卻又被摧砍殆盡
的各類樹木花草。正是執著於種種瑣細私密的個人感官印象,老靈魂原鄉
之行的追尋與失落,便也就在挪用、顛覆舊有(男性)失志、不遇、原鄉
傳統的同時,另闢出女性敘述的無垠天地。《古都》的豐富耐讀,至此或可略見一斑。事實上,自從《我記得》
一書問世以來,朱天心便是學者高度關注的研究對象,每有新作發表,學
院派讀者莫不見獵心喜,磨刀霍霍。她對中外文典、事典及流行資訊的百
般羅織舖排,醞塑出偽百科全書式的敘事風格,也因此成為心理分析、後
現代、後殖民等論述皆樂予勘採,並據以振振有詞的礦藏。《古都》的解
讀,當然也可以被「鏡像」、「凝視」諸說,妝點得教人肅然起敬(書前
的〈序〉,可不就是如此?)然而,學院派的評論(包括本文)儘可高來
高去,玄虛迂闊,老靈魂歷劫轉世,閱人閱事無數,該不會甘心被一二時
興理論、當紅名詞套牢吧?但看她一再叨叨地說:「不願此生就這樣隨隨
便便被發現並就此認定」、「我不只是……」,便可思之過半。而《古都
》,終將以其自具的魅力,啟動讀者多方面的閱讀興味與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