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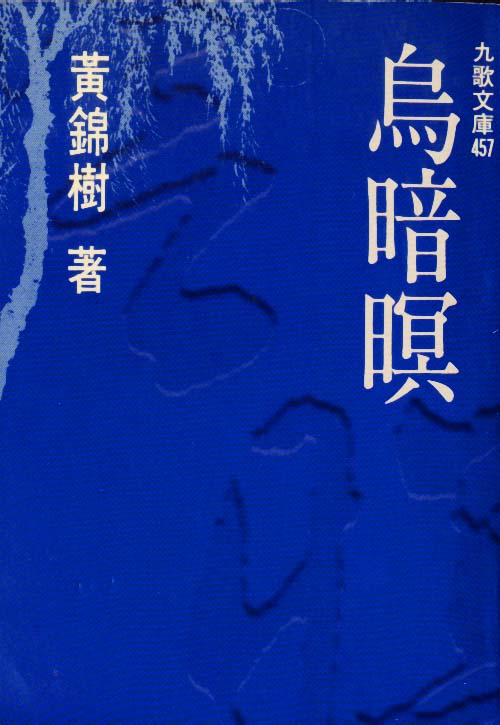
聯合報《讀書人》1997.03.03
黃錦樹是當今文壇最被看好的青年小說家之一,他的備受矚目,不只
在於近年來縱橫於各大文學獎項的傲人成果,也緣於在文學評論上的精到
表現,和意欲「重寫馬華文學史」而「重寫馬華文學」的自覺與努力。從
第一本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到新近出版的《烏暗暝》,其自我追尋和
創作實踐的痕跡,歷歷可見。身為第三代的大馬華裔子弟,熱帶膠林是黃錦樹寫作的原始場景,異
域身分認同的「存在焦慮」和馬華文學史的「經典焦慮」,則是他念茲在
茲、下筆不能自休的主題。正是由於這種種特殊質素的錯綜縈迴,他的小
說創作,遂在披露大馬華人(文學)「內在流離」的同時,也成為一種企
圖重建主體身分的「書寫政治」。初步看來,《夢與豬與黎明》中〈M的失蹤〉和諸多篇名刻意前有所
承的小說,似乎都是藉由後設技巧的大量運用,以體現尋找/否定文學宗
師的「經典焦慮」;而《烏暗暝》的絕大多數篇章,乃是在瀰漫著移民血
淚的族群記憶與歷史想像之中,直視恆處於「他者」地位的「存在焦慮」
。綜觀全書所收的十一個短篇,無論是曾獲大獎的〈魚骸〉、〈貘〉和〈
說故事者〉,抑是散見於各文藝刊物的〈色魘〉、〈山俎〉、〈烏暗暝〉
、〈非法移民〉、〈大水〉、〈血崩〉,在在銘記了唐山移民在膠風椰雨
中與自然環境的搏鬥、在充滿種族岐視的人文環境中戒慎恐懼的生活、以
及發生於革命流血年代的諸般創痛與死亡。然而,儘管故事本身的內蘊沈
重悲涼如許,作者卻迴避了一般(受難者)「我控訴…」、「我記得…」
的敘事姿態,反倒慣由跳躍的敘述、失憶的迷惘、繁複的意象,去拼貼流
離猶疑的內心風景。於是,命運縱使無常、世界容或瘋狂不義,故事中人
,每每只能徒勞於無償的追尋(或逃避),一再留下未了的懸疑與喟嘆。
〈貘〉、〈魚骸〉等文所以撼動人心,未嘗不是繫因於此。其中,〈魚骸
〉藉殺龜取甲寄寓對「大中國」的愛恨情仇,〈貘〉經由瀕臨絕種的馬來
貘喻托華人移居異域的適應不良,〈烏暗暝〉以處於暗夜、迷霧中的惶恐
,隱喻大馬華人的政治處境,亦自耐人尋味。此外,〈膠林深處〉與〈新柳〉兩篇,則另有對「書寫」問題的關注
。〈膠〉文向默默耕耘的馬華文學前輩致意;〈新柳〉為取材於《聊齋》
的「故事新編」,文中角色輾轉輪迴於夢醒莫辨的前世今生,雖是後設手
法的再度運用,卻隱約透露黃錦樹在「存在焦慮」與「經典焦慮」交相煎
逼下的書寫政治:「以你獨特的筆跡,填滿剩下的所有空白」--因而,饒有興味的是,當苦難創痛幻化為興寄繁複的意象,當流離的
身世落實為曲折動人的文學書寫時,一種嶄新的(文學)主體,乃隱然成
形--黃錦樹的小說能否成為馬華文學的經典,固然猶待考驗,但其獨特的
馬華經驗與著意於思辯性的藝術表現,實已風格自具。而如此風格,將會
是他日後更上層樓的動力,抑是阻力?是可以一再超越的基準線,抑是自
我設限、難以突破的瓶頸?且讓有心讀者,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