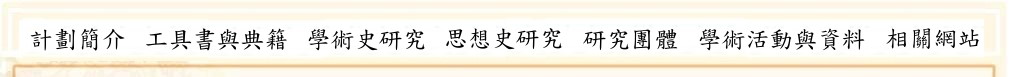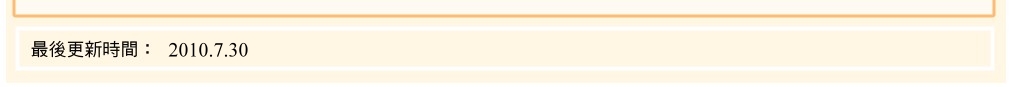貳、東亞哲學的論證與安立模式
陳榮灼:很多年前在臺灣的時候,我跟黃俊傑教授主持過一個國科會研究計畫,是關於中國古代思維模式的研究。當時我們有個共同的看法,就是很可能中國的思維模式是有一個特殊的方式,這跟西方、甚至跟印度的思維模式是有所不同的。基本上我們認為中國的思維模式可能是一種類比的思維方式(analogical thinking)。當時我自己在這些方面研究的一些成果,也是利用了與西方比較的方法,就是用記號學(semiotics)的方法來做切入點,特別是以Charles Peirce記號學作為一個框架。從記號學的觀點來看,漢語跟中文的結構有一些特別的地方。在Peirce對基本記號的三分裡面,首先icon,就是圖像;還有symbol,就是符號;另外一種叫index,就是指示。從Peirce的觀點來講,中文是一種icon。中國文字是象形文字,漢字的構造原則,跟中國的傳統思維模式背後的指導原則是相同的,都是以「相似性」(similarity)作為基礎。「相似性原則」是共通於中國漢字的造字原則和其中的思維模式的精髓。另一方面,西方的思維模式基本上是「演繹的」(deductive)。無論從亞理斯多德的「形式邏輯」到近代羅素的「數理邏輯」,基本上還是演繹型。當然在亞理斯多德著作裡也可以看到觸碰到類比式的研究。但是,作為西方邏輯跟思維模式的主流,基本上是演繹性。至於印度的思維模式,特別可從在中國的傳統之「因明學」的資料來看,基本上因明學是一種指示性的思維模式(indicative thinking)。一個很有名例子,就是「此山有火,因有煙故」。為什麼說此山有火呢?因為我們看到有煙,所以說它有火。煙對那火來講,是一個指示(indicator)。印度的思維模式跟中國的類比思維有相同的地方:它不是一種必然性的推論,也就是說結論所提供的訊息並沒有完全包含在前提裡。與此相反,西方的邏輯或演繹性的思維模式中,一個有效的推論基本上是結論所提供的知識訊息已經全部包含在前提中,否則它是個謬誤。雖然中國跟印度的思維模式都不是必然性的,但因為其結論的消息可以多過於前提所提供,所以它是一種創造性思維(productive thinking),就是說:它可以產生新的知識。今天,特別在哲學界中有一種偏見,就是認為中國哲學沒有論証性進路(argumentative approach)。特別在上一個世紀的50年代,使用敦煌史料來重新研究禪宗時,胡適跟鈴木大拙展開一場論戰。就其中所表現而言,哲學的研究好像只有兩種出路:一種是剛剛黃俊傑教授提到的,文獻學的、歷史的(historical)、考據學的方式,胡適是這方面的代表;另外還有一種是神秘主義,一種比較直觀的、直覺的,這是鈴木大拙的進路。好像只有這兩條的路線在鬥爭。但是如果重新來看中國哲學的歷史,可以發現並不一定只有這樣子。在先秦時代,可以看到當時的學術論辯非常發達,哲學家也有很理性的進行哲學論辯的表現。這個表現的成果導致了《墨辯》的產生。如果中國的思維模式是一種類比邏輯,那麼《墨辯》就是這種邏輯理論之表達。個人因此把《墨辯》作為一種類比推理的理論來重新詮釋。這一類比推理理論可以說是中國邏輯的「體」;而哲學的論辯上的「用」則特別表現在孟子跟告子關於「人性是不是善」的討論上。還有荀子對孟子之批評都是非常理性的討論,其中有非常強的邏輯成分。 吳展良:類比性的表述方式,在古書中很普遍。然而我想提三個問題。首先,研究《墨辯》的大家Graham在他的書中,的確比較是從西方形式邏輯的觀點來看墨學。但是他也提到墨家注意到語言的限制性,所以他說墨家曾指出論述語言的限制會造成我們推論的困難,必須特別加以注意,以免推論無效,這似乎是古人對於何為有效形式推論問題的一種自覺。另外,你剛剛提到否證的問題,在Harbsmeier的書裡似乎也特別談到有關於《墨辯》裡一些否證的例子。他認為中國的傳統思維裡頭,也有跟西方形式邏輯比較近的部分,正是因為墨家注意到否證的問題。這兩位大家都認為,中國傳統思想裡的邏輯性討論,可以拿《墨子》作代表。一般中國思維很可能是關係性的或類比性的思維,但墨家不同。既然您跟他們的看法正好對立,是否要用墨家的文獻對此作更加深入說明,這是其一。其二,一般人會質疑所謂類比性邏輯,它所面臨最大問題是因為它是context dependent。因此,它的推論的有效性是很難在形式上被確認的,這樣它要怎麼來作一個有效運作的推論工具?第三個問題是,能不能請您舉一兩個例子,來仔細說明您所謂的類比性邏輯是怎麼樣的一個定義?因為這個名詞可能容易讓人們誤解。 陳榮灼:先舉個例子。我這只是純粹舉例,沒有政治性的含意。最近有個臺灣團體參拜靖國神社,這個動作好像是猶太人拜納粹黨。這是中國人類比思維來推理的。還有一個最常見的例子,為什麼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可以點燈?這是中國人常見推論的形式。所以為什麼臺灣人參拜靖國神社是不對,這種不對正如猶太人參拜納粹黨。 吳展良:這個例子一般的臺灣人比較容易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類比。 陳榮灼:這只是舉個例子,沒有說它的有效性。如果從亞理斯多德式的「凡人皆有死,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會死」所謂的三段式論述,這樣的話凡是臺灣人不應該參拜,這是從一種比較「演繹性」(deductive)的觀點。 彭文林:剛才吳展良先生講,在中文的推斷模式裡比較需要有context dependent? 吳展良:按照類比式的思維。 彭文林:對,我想在這邊討論,即使是任何類比性的結構,在歐洲人的講法裡一樣是context dependent。 吳展良:對,我就是這個意思。類比性思維的本質會變成context dependent。我是問,如果是這樣子的話,要怎麼樣進行一種比較有效的形式推論?恐怕就困難。 陳榮灼:基本上沒有一般有效形式推演規則。 吳展良:但如果依Graham的講法,《墨子》是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形式推演。 陳榮灼:我覺得這個是不一樣的。因為這個牽涉到「真」(truth)的概念,能否「形構化」的問題。 彭文林:我想藉著這個談一個概念:context dependent不只是類比邏輯上面所涉及的。如果從亞理斯多德的邏輯看來,我想指出兩點。第一,亞理斯多德邏輯的討論裡面,基本上對前項、中項、後項的關係中間有一個概念界線上面的意義,這個概念界線上面的意義一定是在一個context dependent的內容裡談論的。儘管你說把形式抽象化的時候,在實際亞理斯多德邏輯學的應用上是一個基本的角度。第二,在亞理斯多德一般邏輯的推論裡面,基本上是以概念結構,或者是以所謂的名詞當作推斷的材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設想如果我們把人、知識或者是經驗設想成各種邏輯之間的連結關係來推斷。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覺得在中文裡面有個很大的差異,就是我們並沒有所謂的對名詞、動詞在詞語上已經先做了區分之後,在論證上再進一步來推斷的方式。由於這個緣故,就使得某些東西必須要通過經驗內容來決定。 陳榮灼:我先回答你這個問題。我說《墨辯》中的有效是context dependent,乃是因為類比思維背後的基本原理是「相似性」。至於什麼東西跟什麼東西相似呢?這個並不是客觀的,這跟你的intention有關。這裡有一個例子,這比較超出《墨辯》的範圍。譬如說在量子論最早有一個Bohr的理論說在原子世界的結構,是跟我們的行星系統相似的,就是電子環繞著原子核的律動,好像太陽系裡面行星環繞著太陽。這個是他看出來的,這是creative thinking的表現,因為在他之前沒人看到這一相似性的。這完全是Bohr個人創造出來的。而「演繹推理」的context independence,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用集合論的觀點,來把亞理斯多德的三段論重構,而沒有丟掉什麼東西。 彭文林:有丟掉很多東西。 陳榮灼:我是說從有效性的觀點,從「演繹性思維」(deductive thinking)的觀點來講。 彭文林:我仍然認為丟掉很多東西。 陳榮灼:譬如說context free的問題,你可以把論證完全形式化。如All A are B.,All B are C.,Therefore All A are C. 這個ABC是什麼東西我不理。這個ABC可以是「類」(class)或者「集合」(set)。但是在類比思維裡面,它必牽涉到相似性概念,後期維根斯坦所講的家族性的相似性是context dependent。 彭文林:你的談論對我來講只是一種普遍化的活動。也就是說,在形式上面的語言之上給一個普遍的理由,而這個普遍的理由中間有哪些關係,基本上脫離了實質的經驗內容。我認為這是概念的普遍化。 陳榮灼:用你的語言來說,你可以單一批評說他是比較僵化了。 彭文林:我不是這個意思。當然說這個普遍化有它特定的語言區分的意義,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它也就可以說:我只有普遍化的語言,我不需要個別語句上的推斷了。當我推斷蘇格拉底是某一種特殊的人的時候,我不把某一個特殊的人當作一個普遍的概念。我說蘇格拉底是希臘人的話,當然他就牽涉到實質的事。前項、中項、後項的關係是一個是個別的、一個是普遍的,它從個別的跟普遍的關係所形成。 吳展良:仲介的事情就把它概念化。 彭文林:對。但是事實上亞理斯多德的邏輯並不只是講普遍化的問題,他在講個別化的問題在推斷上仍然有謬誤存在。所以我認為,後來的邏輯學家對這些東西的討論上都只注意到像set theory等等,但是對亞理斯多德來講,他還有其他很多東西。 陳榮灼:從理想的觀點來講,西方演繹邏輯發展到今天像數理邏輯(mathematic logic)可以做到全面的符號化(formalization),當然可能相對於亞理斯多德本來的目標是有差距的,所以我說暫時撇開亞理斯多德,而就西方主流的邏輯來講。 吳展良:所以我們在思維模式裡簡化亞理斯多德? 陳榮灼:我只是舉亞理斯多德這個例子,我們的主題在西方主流的演繹邏輯或思維模式。 吳展良:當代做的是亞理斯多德的形式論證,普遍化的形式邏輯。 陳榮灼:當然這樣說我們有點冒險,這可能牽涉到Max Weber所講的ideal type。但是純粹就分類的觀點來看,可以對比出三種不同的基本邏輯或思維模式。雖然我只是強調中國邏輯與他者之差異,但是並不代表中國傳統思維模式裡沒有演繹性,我的目的在於強調演繹性邏輯不是其主流。 李河:我認為這裡主要的論題,一個是為中國傳統思維方式「類比邏輯」找到一個原型。第二,類比邏輯也不完全是中國傳統思維當中才有的東西。這兩點,我覺得大家的意見都沒有分歧。但類比邏輯和中國傳統的自然語言,特別是傳統漢語的自然語言有什麼關係?這裡頭可能就會找到一種相對能夠解釋的關係。我認為類比邏輯和形式邏輯、演繹的邏輯,假定它們的目的都像是亞理斯多德在《工具論》裡頭講的,這個邏輯主要是要證明問題,其實從論證的角度來說,各有各的效力。比如說類比邏輯,它可以通過一些譬喻的方式,通過一些其他的東西,而它的目標,也是要convince,要能取得一致。 陳榮灼:李河先生提到的這個目標比我原來提的更有企圖心。你的論點牽涉到對亞理斯多德邏輯的表達,乃至對經驗的重建。我想在《墨辯》裡面大概是沒有這樣的問題。對你剛剛提到這種「有效性」的概念,其可能涵義是相對於一個「重建」(reconstruction)的目標,看一看能否重新再現原來那個經驗,即更系統性地重建。但這並非我所要說的純邏輯之「有效性」(validity)的概念。 李河:但是重現可能也是一種實驗室理想的重現。還有,因為論辯的目的、說服的目的,在人類學的意義上是塑造心靈。如果你塑造了心靈,當他重新面對事物,那他的東西會重現。而這種重現,沒有實驗室那種準確,但那的確是我們能夠識別的,如您剛才所說的家族類似性。 陳榮灼:我同意你講的這種,我想到傅柯所講的truth telling的問題。中國哲學倒沒有討論過這一問題,但是卻有相類似的概念,就是「傳道」。所謂「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為什麼我會對老師那麼尊重?就是因為從他可以學到很多經驗和知識。所以這個透過老師所授之知識和經驗的相似(analogical),過去的知識和經驗可以一代一代地傳下去,這個相似性跟傳道論道理有關。 彭文林:我請教一個問題。在柏拉圖、亞理斯多德他們使用analogy的時候,有一定的使用情況,譬如說他跟對話者之間不能取得任何實質上面對任何問題主張的共同一致的時候,我們對我們討論的對象不知道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所以這個時機底下在使用analogy。analogy可能有個基本的作用是說,在柏拉圖的〈Republic〉裡講:我不曉得正義是什麼,所以找一個大的對象來探討。像一個字母在一個很遠的地方我看不見,我用一個大的字母擺在我的面前。一個城邦擺在我的面前當作我觀察的起點,終點是我想瞭解城邦這個政府。 陳榮灼:柏拉圖的方式是按比例而進行推理的。 彭文林:對。我們就是要注意到這個情況,就是說亞理斯多德邏輯如果這樣做區分,前四個邏輯的著作我們才稱他是正面的邏輯學著作。〈De Sophisticis Elenchis〉和〈Topica〉談的是類比作為一個討論真理的方式,它不一定成為任何一種能夠證成真理的可能性;而只是說,正是因為我們不曉得真理是什麼,所以我們必須藉由這個方式來問,我所清楚的跟我所不清楚的界線之間關連是什麼?我的問題是,如果類比是這樣子的機能,它是從我所知道的去推斷到我所不知道的時候,要求比例關係之間的相似性。那麼,孟子跟告子的談論,或是《墨辯》裡面的談論,適不適合西方人類比邏輯的談論?在嚴格性來講就有很多不同。 陳榮灼:這裡有兩種推理目標:一種就是如孟子跟告子的論辯中可以見出的要「說服」(convince)對方來達致真理。其次是在《墨辯》中可以見出那種由已知來推斷未知以增加新的知識性的目標。如在孟子與告子的辯論中,其目標只是安立其本身的論題:「人性是善的」。其實,並不是我們每天都需要去論證,這樣做只不過當意見出現不一致的時方有所需要。就跟看病一樣,我們不會每天都看醫生,只是當有病的時候才這樣做。這些都是屬於一種critical control。但是當進行論辯時,則必須遵守一些共同的、共許的原則方可能進行,《墨辯》便是探討這些遊戲規則。但是這些規則也不完全就是約定的這麼簡單,因為它也還要滿足產生的新的知識的條件。 彭文林:但是它實質上並不讓我們瞭解知識,只是因為它從我們知道的地方出發,當作理解一個新的知識的角度。那麼在這個情況底下,它並沒有在知識上真正證明那個由類比所決定的知識。 陳榮灼:對,類比推論之真正的證成(justification)力量在於知識上能夠產生新知。如果回到萊布尼茲對於邏輯的區分:可以區分art of invention、art of justification。基本上,類比邏輯之力量首先顯現在作為一種art of invention(用康德的話講是logic of discovery),至於作為logic of justification其力量並不這麼明顯。 李河:但是這個就是把類比邏輯和演繹邏輯做對比了。像是把自然生產和技術生產、實驗室生產作對比一樣。維科在《新科學》當中專門討論logic是怎麼從logos裡面出來。我們現在一般談到logos,都是在logos裡面理解的。但是logos本身,例如《新約》裡面談的earth beginning,維科對於隱喻、預言、神話,就是在生活世界當中,通過人文學傳遞下來的,很多塑造人心靈一大堆的東西當中,專門討論了許多關於真實的東西。真實的存在包含了尺度。用我們的話來說,我們燒窯磁,這裡頭他有尺度。在傳統當中我們把他叫火候。火候這東西就是一種尺度,但是它是一種非常經驗性的東西,它不是那種實驗室裡出來的。我的意思是說,一個是類比邏輯本身,它能不能產生新知跟理性本身的關聯。 陳榮灼:一般來說,在類比邏輯裡,想像所顯的效用、擔任的角色很明顯。在這裡我只是對比於不同邏輯到不同的傳統思維模式。在中國先秦,哲學特別在儒家裡面也有論辯性學術論辯語言,所謂argumentative discourse。但是今天我們都忘掉了這點,還以為中國的哲學都很primitive,而回到《墨辯》,我們都可以看到它其實是一類比性、論辯性學術語言。 張志強:我提兩個問題。接著李河先生的說法,我覺得您區分文獻學的路徑跟邏輯學的路徑不同,而您認為後來日本佛學研究裡面因明學研究的出現,這是一種邏輯的轉向。我個人認為不是這樣。我認為這涉及到胡適跟鈴木大拙的討論,而胡適跟鈴木大拙的討論要怎麼樣來衡量,我覺得這也涉及到你要怎麼樣來衡量這個東西。你的類比已經把類比形式化了,李河先生也談到說,類比已經形成類比邏輯這樣的思維。然而文獻學的方式也是一個可能的方式。類比文獻學的論證方式跟鈴木大拙所強調的有什麼關係?第二,我們是不是可以說,胡適這種文獻學進路跟鈴木大拙的討論,是在談怎麼樣安置經驗,或神秘經驗這方面的東西。鈴木大拙某一種程度他也不是採用經驗跟神秘經驗相對立的方式。那胡適也只是說禪宗經驗可以用現代學的方式去碰觸,我們不能直接碰觸那經驗。所以我覺得這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傳統知識學術的性格,怎麼來安排這個論證?就是說你談類比這個方式,你這篇文章是把類比的邏輯提出來,而從當中可能可以有一個新的邏輯形式。 陳榮灼:我的意思也不是說類比邏輯是唯一的。其實,即使在文獻學的進路裡,也可以有argumentative的元素,箇中也有理性的成分,不過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經驗的證據。無疑,將文獻學進路過分膨脹可以變成實證主義的路線。當然鈴木大拙也是像你剛剛所講的,跳過比量,即超出比量的範圍,而進入了神秘主義。不過,因明學是源自印度的。而早在中國先秦的哲學活動,已有很強的邏輯性表現,而這可以看成《墨辯》的類比邏輯之應用。 張志強:我想做超出邏輯之外的一些感想。我認為,為什麼要把中國思維方式歸類成類比邏輯,才是對哲學的貢獻?如果要我找到中國思維方式的特殊性,不是要把這種特殊性跟一種普遍的哲學研究的西方方式做一個融合,而是要用合理的方式來表現中國思維方式的特殊性。 陳榮灼:我所做的只是一種釐清性的工作。因為迄今為止,主流的做法都是用形式邏輯來解釋《墨辯》,我擔心這會抹殺了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特質。另外在傳統中國哲學的實際活動中,如孟子跟告子的對話中所出現的論證,都是類比式的,這正好有助於說明《墨辯》本身也是一類比邏輯理論。而從這一立場出發,就可以看出所謂「孟子好辯」這個辯是什麼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