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李弘祺教授為本系系友,1968年自大學部畢業,1974年獲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教授及城市學院教授、系主任,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教授兼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國立交通大學講座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等教職,研究領域為東亞教育史、比較史學。2014年8月自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講座教授退休,現為北京師範大學客座研究學者。 |
歷史教學是一件非常重要且嚴肅的課題。從我回臺灣以來,受到張元學長的影響,偶爾會思考這個課題。我並沒有系統地整理我的思想,但是教歷史已經40年,究竟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所以答應衣若蘭老師的邀請,寫下我參與歷史教學工作的感想。
時間的內在相關性與博覽群書
首先,我認為一個好的歷史學者應該是一個好的知識人,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我相信從事歷史研究,最重要的莫過於認識歷史中各樣因素的內在關聯性。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是近代第一個清楚標榜這一點的史學家。蘭克認為所有的事(也許可以更精確地說是所有「事件」),都是上帝安排發生的,缺一不可,彼此相互效力,一同讓上帝所導演的這齣戲得以開展下去。這就是所謂的內在關聯性(internal connectedness; innere Zusammenhang; 我用的是Peter Gay的英譯)。(註釋1)中國人很早就發展出類似的觀念,即所謂的「感應」:兩個看來互不相關的事件(例如秋天時囚犯死的特別多),事實上卻有內在相互的關係。現代人把這樣的說法視為迷信,當然不算錯,因為它太過強調道德的倫理因果,沒有普遍化到客觀、自然的事物上面,難以令人信服。如果能把它客觀化,強調相互因果的有機關係,就與蘭克的說法相近了。
我以上這段複雜的話,目的在說明為什麼好的歷史家必須是一個「事事關心」的知識人,他必須對每一樣與他所研究的歷史有關的事物都感興趣。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指出中國傳統家族(或宗族)的結構在宋代之後有很大的改變,而這個改變與中國科舉制度的興起有一定的關係。(註釋2)這是一般研究宗族制度的人不曾系統討論過的,所以有的學者不以為然。但是如果歷史學者不能看出兩者之間的關係,那麼他就祇是一個資料的整理者,連袁樞都不如,更遑論傑出的歷史學者了。(註釋3)
| 因此,一個歷史學者要不斷地思考歷史「事件」與它發生的時代之間的關係。一個時代或許是三十年,也可能是一百年,甚至更長。例如我們如果要談印刷術對人類的影響,那麼史家就必須對印刷術的由來,歷代被使用的情形,唐、五代到宋之間的雕版印刷的發達(五代之後又不斷大量印刷佛經,北宋初也印了不少大書),乃至於當時造紙技術的演進都有一些基本的認識。研究印刷術的人不可能對這些知識都有專精的掌握,更不可能全部做過第一手研究,但是他必得要涉獵這些課題的二手研究,以便對探索的題目做出可靠的定位,描繪可靠的輪廓。第二手知識越多,越能做出精密、反映當代現象的作品。這樣還不夠,好的史家更要像一個偉大的畫家──如范寬、李公麟,或像波蒂伽利(Sandro Botticelli)、畢卡索,帶領我們去看常人眼睛所看不到的東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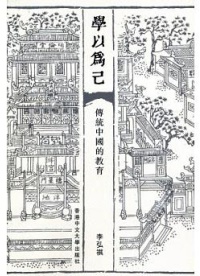
▲李弘祺老師2012年出版二部專著《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卷里營營:歷史、教育與文化演講集》
|
我提到造紙術是有原因的。按照錢存訓的說法,中國的造紙技術發達,使得紙張的供應遠比西方經濟(便宜),是促成中國印刷術(特別是活字印刷)的使用早於西方的重要原因。這就是為什麼我說要瞭解中國印刷史,也要對造紙術有一些興趣及認識。
印刷術的歷史橫跨好多個朝代,史家因此要對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歷史有心理準備,盡量多讀、多涉獵,使自己的瞭解能更接近歷史的真實。當然,人生而有涯,而知也無涯,不可能讀完天下的書,到了一定的境界,史學就像是藝術一樣,看的是天賦、靈感和聯想力,別無他法。但這是在努力耕耘的基礎上面講的,才氣不是無端而來,絕對是建築在長年積累的經驗和廣泛的閱讀之上。所以歷史學者的成熟需要時間培養,與數學家迥然不同。這一點不用我多說。
好的史家因此就要常常反省如何選擇好的、有用的書。然而就算懂得如何選書,也還是有讀不完的書。對一個忠實的史家來說,任何研究課題都有數不完的書要讀。研究不同題目的學者,所選讀的書自然有所不同。一個懂第二、第三外國語的學者,比一個衹懂第一外國語的人也因此佔有更大的便宜,因為他可以選擇的書範圍大很多。
眾說紛紜與歷史真理
這一來,史家對同一件歷史事件,就會有不同的看法。那麼人類將如何找到可靠的真相呢?中國人總是從「蓋棺論定」這句話著眼,好像一個人或一件事一旦修入正史,就可說是「論定」了。一般言之,中國正史是一個偉大的傳統。但是現代人研究歷史,卻不衹從歷史學到為人的道理及倫理道德的教訓,我們還希望知道很多其他知識:例如朝廷決定貨幣發行量的政策及其背景,或者劃分社會階級所反映的哲學基礎。這些都與社會經濟的健全與否有莫大的關係。主事官員即便心術正,也未必能營造健全繁榮的經濟環境或維持階級間的和諧。中國人或許很懷念悲劇英雄,但是悲劇英雄對改善當代社會問題卻往往不一定能做出真正有價值的貢獻,甚至可能做出不正確的判斷。
|
我的意思是「蓋棺論定」的記載也未必能提供我們希望知道的歷史真相及正確的解釋,因為後代研究歷史的人所問的問題與第一手資料的關心常常並不一致。在西方,大概從17世紀開始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因為他們感到歷史記載有很多不可信,特別是《聖經》(又特別是猶太教的《希伯來聖經》)。從懷疑《聖經》的歷史記載開始,他們拓展了歷史研究的視野,促成了考古學(古文物學)的興起。同時,人類知識的範圍日益擴張,開始問過去不曾問過的問題,包括地理對歷史發展的影響,政治體制與國家大小之間的關係等等。到了19世紀,學者們更深入地發問人類是不是可能知道歷史的真實。這種知識論的問題現在變成很重要的史學課題。 |
從以上所談的中西歷史學者對歷史真相及解釋的看法,讀者可以看出一般史家心中大概都有數,就是歷史知識很難達到真實的境界,懷疑有什麼解釋會垂之久遠,變成永恆的真理,絕對不會被推翻。不過一般史家大概都不會說沒有歷史真理,就是我也相信絕對有一個最終的真理,祇是現在還沒有找到。所以有時我覺得自己很像黑格爾,因為他認為歷史的真理會在歷史結束時完全顯現出來。總之,後現代主義興起以後,對史家的確造成相當的困惑。
我認為今天歷史學者心中有很大的苦惱: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此,歷史學者必須非常謙虛,承認目前我們還沒能擁抱真理;不管是誰寫的歷史,都得要在一定的時間之後重寫。不要以為最簡單的記載就不會被懷疑或改正,而改正的就一定不再被挑戰。在美國被當作兒童教材的華盛頓砍斷櫻桃樹的故事,現在絕大部分的史家都懷疑它的真實性。這麼小的歷史「事件」,我們都無法確定,而它還被當作為人要誠實的歷史教訓,豈不是非常荒謬?十幾年前,將要進入西元2000年,許多學者懷疑西元紀年法,因為現代人1582年才開始使用格列哥理曆(Gregorian Calendar),之前西方人主要是用凱撒訂下來的朱立安曆(Julian Calender)。兩種曆法不僅一年的長度不同(雖然誤差甚少),何年置閏,何時是春分(這一年提早了10天),也都有所歧異,很多以前記錄的年代或日期必須重新推算與更正。但是以前的材料怎麼改得完?何況新的考古挖掘也不斷增加我們要參考、研究的素材。西元2000年時,有些學者關心這件事,因此想要推算一些舊的年代。這一來,有些書使用的年代就與我們向來認知不同:例如過去將巴比倫消滅猶大國(以色列的南國)的年份定在西元前586年,但是現在有許多教科書改為587年。(註釋4)又如鐵錘查理(Charles Mattel, 686-741)在法國南部的杜爾(Tour)打敗伊斯蘭軍隊的年代,一向定為西元732年,現在有人主張改為733年。(註釋5)由此可以看出日期的推定或換算,就可以造成很多困擾,根本是一門大學問。我們信以為真的、最簡單的紀錄都可能出錯,更不用說對歷史進行綜合性的大解釋了。
有的人或許會認為年代可以用細心、精密的演算來確定,但是問題並不這麼簡單。除了因為我們對於古代曆法的瞭解不夠完善之外,當時人的計算也未必可靠,用現代精密的計算可能產生「不符合」他們根據粗略曆法算出來的日期,(註釋6)所以現代人常常必須用其他同時代發生的事件的日期來比對,從而得到一個比較合理的、用現代曆法可以表述的答案。
 |
有的讀者不免要問,年代或日期這麼重要嗎?說真的,我也不敢說一定是。但是難道要歷史學家承認它們並不重要?例如過去對商王的先後次序大多是根據司馬遷的《史記.殷本紀》,從來沒有人提出疑難,因為我們對古代的曆法知道的很少。近代以來,人們有了考古學的知識,又因為天文學的長足進步,有能力系統地收集古代對天文觀察所留下來的紀錄,輔以精密的計算,(註釋7)於是可以做古人所做不到的比對、校勘,來檢測《史記》的記載。從孫貽讓,經羅振玉、王國維等人,發現《史記》的記載雖然大致可靠,但是商王先後的次序、商周更遞的年代,也還是能提出新的、更為精密的計算(雖然仍有很多爭議)。當然,加上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新發現,我們甚至於可以對商周斷代提出許多新觀點。(註釋8)這就是史家堅持對一切即使是很簡單的記錄都不放過檢驗的原因。 |
從史家要謙虛說到歷史教學
因此史家一定要謙虛,這一點十分重要。它反映的是歷史學問和解釋的眾說紛紜,以及長江後浪推前浪的現實。我曾在我一本書的序裏,嚴肅地說這是我個人研究的結果,反映個人意見。結果有人卻就這點大做文章,言下之意好像是我的書不用一讀。能不能成為一家之言,自然不該信口胡謅,但我的書竟因此被解釋為不是嚴謹著作。
歷史會不斷地改寫,史家要有這樣的警覺。有的書用了幾十年,像錢穆的《國史大綱》,這是因為在港臺,大家喜歡它的精神和歷史哲學。至於它的內容和結論,其實有許多可以檢討的地方。我這麼說,當然有人不同意。這也沒有關係,衹要想到我說的話也會被忘記,就無所謂了。
我上面的冗長討論是要引入歷史教學的問題,特別是歷史概論或入門的通史書該如何選擇的問題。就臺灣言之,普遍使用的教科書是錢穆的《國史大綱》。我初入歷史系,用的則是傅樂成的《中國通史》。顯然,錢穆的書帶有強烈的民族使命感,是一本令上一代經歷過抗戰的中國人血液沸騰的作品。這是傅樂成的書所比不上的。此外,「西洋通史」雖然也是必修,但是我看不出有什麼教科書能像錢穆的書那樣令人興奮激昂。問題是:之後修讀專史或斷代史,學生學到的就與大一所學的史觀或對史學的興奮感不再有聯繫,這是很大的問題。當然,或許這並不一定不好。因為正如前述,歷史系的學生應該準備面對「學問會與時俱進,解釋會不斷修正發展」的挑戰,而不要感到挫折。如何讓學生取得這樣的態度呢?更精確地說,要如何發展學生批判和獨立思考的為學態度呢?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時,高中生準備會考及參與兩所公立大學(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的入學考試,通常使用《國史大綱》和郭廷以的《中國近代史》。但港大歷史系教的是世界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史(中國古代史則在中國文化研究學系教),因此想考港大歷史系的學生,大多會再讀芮瑪麗(Mary C. Wright)的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同治中興:中國儒家的最後抵抗》)。這三本書大概是準備申請歷史系或以歷史成績申請大學的高中生所使用的主要書籍。我想讀錢先生書的人,可能根本不能接受芮瑪麗的書對儒家的看法。事實上,就連郭廷以的史觀恐怕也與錢先生大相徑庭。應該如何整合這些不同的觀點呢?
再說,有人將來要讀西洋史,就當時的香港言之,這些人大概不會仔細研讀《國史大綱》,改而修讀David Thomson的Europe since Napoleon(《拿破崙以後的歐洲》)。這本書風靡全世界,因為它的史觀不算尖銳,而且文字流暢,讀起來十分容易吸收,作為入門書,的確引人入勝。它所介紹的基本史實也容易把握,能反映當時大部分英語世界史家們的觀點。此外,它還可以銜接學生後來要讀的專著,是一本難得的教科書。
看過兩地的比較,讀者應該會問:究竟歷史教學的基本目的是在灌輸學生一組可以持之久遠的史觀,還是教導基本的事實,瞭解當前史學界對歷史研究所得到的成績呢?我認為臺灣(或說國民黨體制下的)歷史教學大概仍然是堅持史觀的建立,甚至於強調或至少贊成要由政府來主導,接受一套政府所偏愛的史觀。這樣的作法在今天臺灣民主社會裏明顯已經遇上極大的困難。前一陣子政府要「調整」中學歷史課綱,果然引起很大的風波。我已經在別處發表意見,就不在這裡重述。(註釋9)不過,我還是要強調一點:參與修改課綱的學者或未參考學界最新研究成果,教育部的作法還是有待商榷。
我主張政府應該退出課綱的編制,讓史家在史學的潮流和進行研究成果時得以自由發揮。歷史教學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學生知悉老師們的關心所在,當前歷史學術發展的趨勢,以及歷史學家如何發掘課題和作出結論。學生不應該全盤接受老師的結論,以之為經典,依賴它們來安身立命。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歷史系學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訓練自己廣泛閱讀,並利用由此得來的知識,進行獨立的判斷,做出自己的解釋,同時反映多數史家的意見和反映創新的看法與解釋。若能寫出這樣的著作,應該可以贏得同時代大部分史家的認同。在這樣的過程當中,好的、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課綱自然會浮現,而這個課綱也一定會是當代最好的歷史學者所寫出來的,政府根本不用擔心沒有最好的課綱提供給國民使用。
|  |
我的結論很簡單,那就是歷史學就像藝術或音樂,是建立在積累的經驗和廣泛的閱讀上,透過探索史實間的內在關聯,培養出批判的眼光和解釋的睿見(想像力),好不斷改寫舊觀點的一門學問。好的歷史作品會反映當代人的關心和對未來的憧憬,協助人類創造更為美好的世界。史家的責任因此非常重大,而態度必須謙虛,歷史教學也應該反映這些高尚的特質。
註釋1:我們可以確定蘭克在他一生的著作中祇用過這個詞一次,在他的Sämmtliche Werke, heft. 53-4, s. 564,但是因為後來的研究者常常強調它,所以變成了重要的觀念。
註釋2:李弘祺,〈中國科舉制度與家族結構的改變〉,收入氏著,《卷裡營營:歷史、教育與文化演講集》(臺北:允晨文化,2012)。
註釋3:我個人是把袁樞看得很高的,因為他可以說是第一個系統地思考歷史因果關係的史家,而不祇是抄《資治通鑑》的一般讀書人。
註釋4:事實上,我們對這麼久遠時代以色列人的曆法瞭解還不是很充分,學者一直認為應該在西元前587-586年之間。現在主張要改,其實徒增困擾。
註釋5:學者們對於發生的月份(10月)大致沒有爭執,但對日期則又有不同的意見,最流行的說法是10日,也有說是1日或25日的。
註釋6:這使我想到一個有趣的說法:原作者沒有根據翻譯來寫他的原文。
註釋7:例如奧伯澤(Theodore von Oppolzer, 1841-1886)編著的《歷代日蝕大全》(Canon der Finsternisse),於1887年出版,該書列出從西元前1207年到西元2161年間13,000個日月蝕的發生時間。
註釋8:以上所講有關商周斷代的問題,牽涉的知識很廣,問題十分龐大,我引用它,衹是用來解釋歷史研究的複雜,絕無我是專家的含義。十餘年前,中國推動了一個「商周斷代工程」,結果無法證實,亦未發表研究成果。
註釋9:參看〈關於歷史課綱問題的幾點觀察〉,http://www.chappaqua.blogspot.tw/2014_02_01_archive.html;以及〈關於歷史課綱問題的幾點觀察〉,http://gospel.pct.org.tw/AssociatorMagazine.aspx?strTID=1&strISID=142&strMagID=M2014062003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