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平(UCLA扣岑考古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臺大歷史系碩士)
| |
按:史嘉伯(David C. Schaberg)教授是當今西方學界研究古代中國文本,尤其是《左傳》,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大學時期就讀史丹佛大學比較文學系(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anford University),1986年畢業後赴臺,在臺大中文系進修中文至1988年;1989年進入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攻讀,1996年取得博士學位。目前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與文化系(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CLA)教授,兼任該校人文學院院長。所著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1]榮獲2003年亞洲研究學會頒發的列文森獎(Joseph Levenson Prize of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史嘉伯教授是筆者博士論文的指導委員之一,筆者於2017年返臺撰寫論文之前採訪老師,茲將採訪內容轉錄如下,以饗學友。
採訪日期:2017年7月11日上午
採訪地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文學院院長辦公室
|
壹、學思歷程
李修平問(以下簡稱李):您是何時開始學習漢學?
史嘉伯(以下簡稱史):18歲時,我在史丹佛大學開始學習中文。不過,最初有學中文的念頭,是在1982年的夏天。當時,我已經開始學習其他的語言。我有一位要好的朋友正在學習西班牙文,程度相當好。或許是年輕好勝,我跟他打賭,要學一種他不會的語言,而且是可以跟「活人」說話的語言(按:史氏曾學過古希臘文與拉丁文)。於是,我開始考慮學中文。之後,在我倆一起旅行途中,我發現了一本書──《自學中文》(Teach Yourself Chinese)。一時興起,我買了這本書,並在接下來的兩、三天內,用這本書來學習。朋友見狀,澆了我一盆冷水,說我不可能用這本書學會中文。不過,我自己覺得很有用。無論如何,進入史丹佛後,我開始正式學中文,而且非常投入,我極享受學中文的過程。
大學二年級時,我參加一項由史丹佛大學、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共同舉辦的「亞洲志工」(Volenteer in Asia)計畫,因而來到臺灣。當時,我住在臺北的寄宿家庭,一邊在基督教青年會(YMCA)教英文,同時學習中文,並開始學習古代漢語。後來我接觸了《古文觀止》,並從《左傳》入手;《左傳》的故事深深吸引我,使我對古代中國產生興趣。進入研究所後,我大量學習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並以此為基礎,比較古代中國、古希臘與古羅馬文本的異同與特性。我也花了很長的時間,研讀《左傳》及諸子百家。
李:比較文學的方法,是您的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論之一。學習古希臘文或拉丁文的背景,如何對您研究《左傳》及其他古代中國的文本帶來啟發?
史:當我們學習新的東西,特別是背景不同的材料時,自然而然會想要比較其中的異同。如果我們透過比較文學的眼光,來研讀古代中國的文本,一些有別於傳統的研究課題,便會逐漸在心中萌芽。比如說,古代希臘史家赫拉克里德斯(Heraclides Ponticus, ca. 390-310 BCE)宣稱自己曾經到過某些地方的論述,古典學家早就對其真偽有過激烈的爭論;換言之,對於古代希臘史家宣稱如何寫成文本的自述,古典學家已經提出強烈的質疑。那麼,我們就會得到啟發,透過不同的視角,重新分析古代中國文本裡類似的記述。舉例而言,面對古代中國的歷史著作,不論是《左傳》或《史記》,我們應當思考左丘明與司馬遷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又如何為自己作品的真實性辯護。
另一個重要的例子,古希臘與古羅馬的文本,在形式上大多是公開演講的內容,或是教導人演講或辯論的範本。回到古代中國的經典,我們會問,這些文本是否也跟演講有關?是否也作為範本,教導人們如何演講與辯論?就目前看來,古代中國的文本看似是在宮廷的公開演講。
再者,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為什麼古代中國的紀傳體如此呈現?跟古希臘與古羅馬的文本相比,為什麼古代中國的紀傳體這麼與眾不同?相較之下,紀傳體在古希臘與古羅馬的史書體裁的重要性遠不如中國。此外,當我們觀察司馬遷的文體,可以隱約感覺,他似乎承自某個知識體系或書寫傳統,但同時他也創造了紀傳體這種文類。他所承襲的知識體系或書寫傳統又來自何處?透過比較文學的視角,我們會想到不同的問題,嘗試從不同的角度來處理、解釋這些課題。我認為,比較的方法非常有用,不僅可以問為何不同,也可以問何以相似。
我經常想,當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在政治上,中國再度躋身世界性的強權;在學術上,古代中國的研究與其他不同區域的研究逐漸整合。古代中國不僅影響其他區域的走向,其他區域也持續影響古代中國的發展。對於學界來說,這真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時刻,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來自不同區域的材料,跨越國別進行討論,也具備更全面、清晰的視角以重新探索各地的古代文明。
貳、認識文本
李:您認為,作者真的有可能透過文本,精確地傳達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遙遠的古代?
史:我認為作者可以透過文本來傳遞他們的想法,即便在古代也是如此。如果現在我們希望正確地理解他人寫作的意圖,必須清楚明白作者書寫的情境與脈絡。比如說,你明天發電子郵件給我,附上今天我們對話的文字稿,我不但能理解這篇文本的內容,也能清楚明白製作文本的脈絡,甚至糾正其中模糊不清以及有問題的部分。假如,我拿起一篇2500年前的文本,就如同將塵封千年的文物從土裡取出,我們除了有這件美麗的文物外,還可以對它進行更多的研究。當然,如果我們沒有這件文物的出土脈絡,研究的角度與層次會受到較多的侷限,文本也是如此。文本可視為演講的回音,當古人發表演講後,這個事件就消逝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我們仍可以試圖透過文本,一窺演講的內容,但是無法一字不漏地瞭解演講全文。這個觀點,即便在後現代主義興起之前就已受到學者關注。
李: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古代文獻?它們是忠實地記載了歷史?還是後人編造的結果?
史:面對所有的文本,我們都應該問相同的問題:這部文本始於何時?文本中哪些是最古老的部分?這得根據不同文本的實際情況下判斷。當然,我不認為所有古代文獻都是後人編造的。就我個人的理解,所有文本皆應視為文物。因此,學者可以根據現有的證據,討論文本的時代與來源等等問題。必須指出的是,近幾十年來,學界關心的課題已經從如何表述、詮釋文本的內容,轉變為如何在考古材料所建構的古代世界框架中,重新理解文本的位置與意義。這樣的轉變非常重要。然而,儘管考古材料在某種程度上,忠實、準確地提供更多訊息,但仍有許多問題無法透過考古材料解決。
李:因此,就青銅銘文而言,不應當只專注於銘文本身,還必須考慮其考古脈絡。
史:對。一件鑄有銘文的青銅器,本身就包含大量的訊息,如果又有清楚的考古脈絡,其所提供的資訊量,便遠遠超越銘文本身所呈現的內容,這是非常理想的狀況。然而,文本本身就是被設計成可以轉移於不同的載體之間,出現在青銅器上的同一篇文本也可能出現在別的載體。換言之,文本有其自身的傳布方式。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即一些被後世認為非常具有權威性的本文,可能在其原始脈絡中並非如此。所以,我認為青銅銘文是個非常好的例子,有助於我們思考出現於不同載體的文本,它們的起源、功能、意義與傳布等相關問題。
李:可能透過傳世文獻或出土文獻,重建古代中國的歷史嗎?特別是夏或商的歷史?
史:我們能做的,是嚴肅、認真地建構一套牢靠、無法被證明是錯誤的論述,不能被其他人挑戰說:「嘿,等一下,這是錯的,因為有明確的反例。」其次,如果你說的重建古代中國史,是能明確的指出在西元前1050年,或其他特定的時間點,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件,我想我們辦不到。不過,我們仍能透過文獻,進行許多研究,致力建構一套無法證明是錯誤的論述。
就夏而言,我們必須清楚明白要問什麼問題。我想,我們應該問的是:是否真有一群人,作為統治集團,而且自稱為夏?此外,這群人是否對後世有所影響?周人便認為這群人曾經做過某些事。後者是一個合理的問題,我們也可以利用某些證據來回答。現在,學者已經透過更多的證據,試圖尋找答案;而且證據的範圍,早已超越傳世文獻,諸如《尚書》、《左傳》所記載的材料。如今,沒有任何人可以僅僅滿足於傳世文獻所提供的證據,並且說:「瞧,這裡寫有夏,所以就有夏。」在考古學上,或許有可能試圖尋找是否真的有一群自稱為夏的人。不過我認為,時候似乎未到。但我們已經掌握更多的訊息,可以提出一些更合適、更細節的問題,並且可能得到更精確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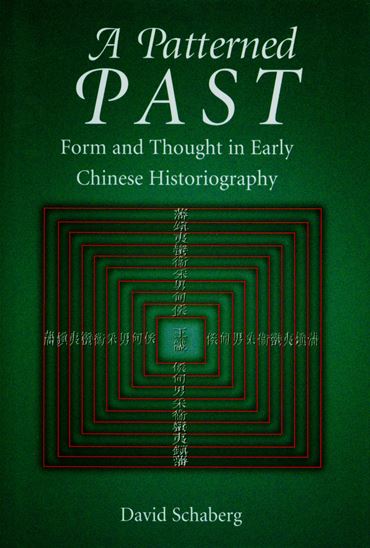
▲史嘉伯老師2001年出版之得獎專著:
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
參、學界觀察
李:2001年,您曾寫過一篇關於《劍橋中國上古史》的長篇書評,[2]文中介紹並深刻反思當時西方學界對於古代中國研究的概況。近年來,您對西方學界關於古代中國的研究,是否有一些新的觀察或想法?
史:近20年來,西方學界越來越多學者對出土文獻充滿興趣,開創許多有別於以傳世文獻為基礎的議題。2001年,當我的論著A Patterned Past出版時,[3]以傳世文獻為基礎的研究,相對之下仍蔚為主流,我的論著就是以《左傳》為討論中心。10年過後,許多人(包括年輕學者)更喜歡研究出土文獻,如郭店楚簡。我認為這樣的發展是一件好事,因為研究出土文獻,期待也要求研究者,必須具備釋讀出土文獻的能力,是一門專門之學;此外,還涉及許多理論層次的問題,像是出土文獻的真實性,以及與傳世文獻之間的關係。目前不論西方、中國或日本的學者,都致力於研究類似課題,這是不同學術傳統間的重要交集。我的好朋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的顧史考(Scott Cook)教授,長期從事出土文獻的研究,也跟中國的學者關係密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以與20年前相比,特別是文獻學,西方學界研究古代中國的風氣已有所不同。不過,我認為過去討論的大問題,至今仍然重要。
另一方面,現在的中國學者在研究古代中國時,已清楚意識到與全球學界接軌的重要性。今日,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間有緊密的交流、更多的合作計畫,不再是各自閉門造車、不相往來的局面。近年來,當我參加學術研討會時,我發現自己與中國學者之間有更多共通話題。
李:就您個人而言,什麼是大問題?
史:首先,我仍對為何某些文本會成為經典感興趣。經典如何產生?經典彼此之間關係為何?如何賦予出土文獻更好的脈絡,以理解傳世經典在原始情境中的意義與價值?其次,如今我們是否可以跳脫司馬談(?-110 BC)故事的窠臼?他對古代歷史的認識,有堅實可靠的基礎嗎?新材料的發現,幫助我們從更複雜且具批判性的角度,反思過去對於古代中國知識結構的認識。我想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與李旻教授的研究,提供了更合適的脈絡,讓我們重新看待先秦文獻在古代的意義。因此,我衷心期盼,我們可以更細緻地討論古代中國的文化,特別是文本所扮演的角色。
就我自己的工作而言,我依舊非常關注演講的研究。例如,人們如何學習演講?他們做哪些努力,改進演講的技巧?好比引用更多的文本?我認為,文本自身就是非常好的範本,教導人們如何繼續產生文本,不論它是演講,還是書寫。
肆、展望與建議
李:恭喜您,《左傳》的英譯本2016年正式出版![4]您未來有何計畫?
史:我手邊還有一部書稿,內容是關於古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準備演講,已經完成數章的草稿,不過拖了幾年,還沒有機會整理與增補全書的內容與體例。我會繼續完成這本書,重新檢視所有證據,也進一步思考演講者——也就是專業演說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我的觀察,古代演講的藝術,在中國學界似乎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這個主題,恰好可以透過比較文學的方法來進行研究。對我來說,作為一種工具,古代中國文字發明的目的很可能就是為了記錄演講內容,甲骨文或青銅銘文都是如此。其次,不論是《左傳》或《尚書》,很多文本其實都在記錄演講的內容。換言之,這些演講內容皆可作為範本,教導人們如何演講。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是,《戰國策》本身並非歷史論著,而是一本收錄策略性演講(strategraphic speech)的彙編。以此為起點,《戰國策》啟發我們反思其他古代文本的功能與性質。例如《韓非子》顯然就是一部軼聞彙編;而《新序》與《說苑》也收錄許多發人深省的道德故事。這些文本收集大量軼聞,目的何在?如果我們從準備演講的角度切入,試想這些軼聞集的功能,其實是為了幫助人們學習演講的技巧,我們對於文本的性質,將會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李:最後,對於有志於研究古代中國的青年學子,您有何建議?
史:我想,孔子是對的。他經常透過一些問題,試圖讓學生、後進不停地思考。求學之道,亦復如是。關鍵在於,我們該如何發掘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問題。我認為,尋找問題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廣泛閱讀。這就是我的人生,讀、讀、讀。於是,我發現了《左傳》,並且意識到這就是我要全力以赴的方向。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大量資料垂手可得,是這一代年輕學人所具備的優勢。儘管他們熟悉這麼便利的工具,有時卻不知該如何妥善運用。為了訓練自己,最重要的事,還是必須回到文本,讀、讀、讀。自由、寬廣地閱讀,發現真正令人興奮的事物,也唯有如此,我們才可能找到真正有意思的問題,做出真正有意思的研究。當然,還得找到一位適合自己的老師,對你的問題感興趣,然後跟隨他認真地做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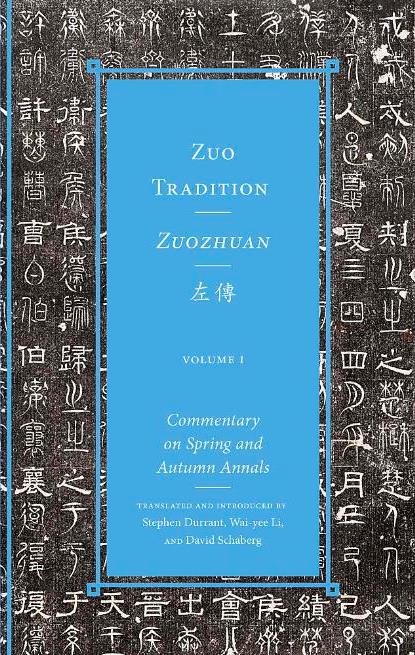
▲《左傳》英譯本 Zuo Tradition / Zuozhuan: 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由史嘉伯老師與 Stephen Durrant、李惠儀二位學者合著, 2016年出版。
|
| 
